斯坦福夫妇去世时曾留下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卖地,所以,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当初“农场”的原貌。校园横跨6个行政区,49英里公路,4.3万多棵树。虽然校园用地日趋紧张,但2/3的土地仍然保持开放。我们来到斯坦福,正处在夏季与秋季之间的假期,偌大的校园更显得空空荡荡。走累了,随处都能遇到一处小树林,在树下的长椅上长长地睡上一觉。
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斯坦福是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他说。
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西岸特有的精神气质。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不可救药的乐观。
“在这里,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阙宗仰告诉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雅虎、Google、苹果……都是一两个人,但具备了影响了全世界的能力。这不仅是斯坦福,也是整个硅谷给人的感觉。”
半年前,28岁的阙宗仰(William Chueh)刚刚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上周,他和SLAC首席科学家沈志勋、纳米之父保罗(Paul Alivisatos)一起吃晚餐,他说“我听他们晚餐之间的谈话。他们所谈之事的远见,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沈志勋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William,20年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大型的计算问题?现在做基因的计算,需要大型的电脑设备,要有几千台几万台电脑连在一起。会不会像Google一样,云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因实验都在云端计算?”
保罗问了另一个让他很震惊的问题:“瑞士正在做超级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那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做的实验。William,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用1%的成本,在旧金山做这个实验?”
阙宗仰的研究方向是大型能源转换与储存。“世界上一共有三种能源:太阳能、化学能、电能。除了核能之外,太阳是唯一能解决地球能源问题的。太阳一天的能量就能供地球用一年,问题在于没办法储存。电池的价格、能量密度太低,支持一辆车也许可以,但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城市怎么办?”
他们的想法就是先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比如氢、甲烷、乙醇、丙烷,可以大规模储存和运输,比如在撒哈拉沙漠把太阳能存成化学能,然后运到芝加哥,或者东京。但就日常使用而言,化学能量还是得转换成电能,所以他们要研发燃料电池,能很高效率地把化学能再变回电能。“我们希望做的比引擎还要小,但就像一个黑盒子的发电厂。进来是乙醇,出来是电,里面的运作决定了效率和污染程度。”
“如果你要影响全球规模的能源转换,不能只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地解决,而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转换。所以我们想研究的,是大型的能源转换的东西,不是一瓦两瓦,而是兆瓦。”
“我们的研究90%是要失败了,但一旦成功了,就必须具有影响全球的能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斯坦福是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他说。
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西岸特有的精神气质。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不可救药的乐观。
“在这里,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阙宗仰告诉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雅虎、Google、苹果……都是一两个人,但具备了影响了全世界的能力。这不仅是斯坦福,也是整个硅谷给人的感觉。”
半年前,28岁的阙宗仰(William Chueh)刚刚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上周,他和SLAC首席科学家沈志勋、纳米之父保罗(Paul Alivisatos)一起吃晚餐,他说“我听他们晚餐之间的谈话。他们所谈之事的远见,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沈志勋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William,20年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大型的计算问题?现在做基因的计算,需要大型的电脑设备,要有几千台几万台电脑连在一起。会不会像Google一样,云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因实验都在云端计算?”
保罗问了另一个让他很震惊的问题:“瑞士正在做超级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那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做的实验。William,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用1%的成本,在旧金山做这个实验?”
阙宗仰的研究方向是大型能源转换与储存。“世界上一共有三种能源:太阳能、化学能、电能。除了核能之外,太阳是唯一能解决地球能源问题的。太阳一天的能量就能供地球用一年,问题在于没办法储存。电池的价格、能量密度太低,支持一辆车也许可以,但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城市怎么办?”
他们的想法就是先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比如氢、甲烷、乙醇、丙烷,可以大规模储存和运输,比如在撒哈拉沙漠把太阳能存成化学能,然后运到芝加哥,或者东京。但就日常使用而言,化学能量还是得转换成电能,所以他们要研发燃料电池,能很高效率地把化学能再变回电能。“我们希望做的比引擎还要小,但就像一个黑盒子的发电厂。进来是乙醇,出来是电,里面的运作决定了效率和污染程度。”
“如果你要影响全球规模的能源转换,不能只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地解决,而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转换。所以我们想研究的,是大型的能源转换的东西,不是一瓦两瓦,而是兆瓦。”
“我们的研究90%是要失败了,但一旦成功了,就必须具有影响全球的能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由Admin于周六 八月 31, 2013 7:01 am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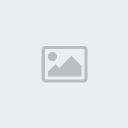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