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迪南德•沃尔特•德马拉二世毕生都在伪装他人。与他相比,靠冒充飞行员、伪造支票骗取了几百万美元的阿巴格奈尔(电影Catch Me If YouCan 的原型)只能算个俗气的二流货色。
德马拉1921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父亲曾拥有一家知名的电影公司。家道败落后,他个性中的敏感、骄傲渐渐发展为烦躁、任性。14岁时,他从中学出走,开始了漫游,先在罗德岛一家修道院待了几年,随后进了部队。
德马拉具备观察和利用制度漏洞的天赋。在部队时,他有办法逃过繁重的劳动;只要戴上一个快递员臂章,他就可以走到食堂长长队伍的前面,最先吃到热饭。军旅生活对他来说太过无聊,1941年12月4日,他偷了一张身份证开了小差。三天后的早晨,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军队开始搜捕逃兵,德马拉做了个奇怪但精明的选择:重新加入海军。
他在海军医学院完成了基础医学课程。由于没有高中学历,他只能被分配去荒岛做陆战队医务兵。面对这样的安排德马拉可不甘心,于是他偷了几份学院的档案,使用一个姓弗伦奇的医生的履历申请做军医官。军方很快给他授衔。然而,当他了解到部队还要对他进行治安审查后,就把一封遗书和军帽留在海岸上,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营地。这一年他刚满20岁,高大强壮,面相比实际年龄沉稳老练,学会了不把内心的慌乱表现出来。
德马拉对宗教抱有浓厚兴趣,离开军队后他打算直接从主教做起。他继续使用弗伦奇医生的履历,先后在26个不同教派的宗教团体里厮混过,每次都引起修道院院长或大司铎的怀疑。其中一次,他已经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神学院研究生的课程,但因为不满自己的教职,直接偷了院长的证件逃往南方。
又被几家神学院和修道院识破以后,1947年,德马拉在华盛顿再次走运,为圣马丁修道院筹建心理学系,并进入了当地的权贵阶层。这年夏天,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两次逃脱兵役把他从修道院带走。
在法庭上,德马拉运用从教会学来的动人口才向法官忏悔:6年来,宗教生活已涤清了他的心灵。在赢得战争的美国,人们相对宽容,他被判了6年监禁,最后只服了18个月刑。
德马拉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出狱后,他晚上在医院上班,白天在一所法律学校听课,但他无法容忍从系主任到旁听生的落差。1950年,他使用约瑟夫•塞尔医生的名号,前往加拿大报名参加朝鲜战争。塞尔医生确有其人,德马拉曾经复制过他全套的毕业证书和行医执照。在新布伦瑞克的加拿大皇家海军兵站,医院夜班看护德马拉用了两个小时成为海军上尉约瑟夫•塞尔。他把自己塞进一套崭新神气的镶金边蓝色制服里,无忧无虑地前往海港报到。
那将是他一生中最奇特和浪漫的年头。
在海军医院时他干得不坏。他学过基础医疗课,知道有一半的病不用治疗就能自愈;对于另外一半,他使用大量抗生素,再治不好,就把责任推给最近的一个医生。当被安排到一艘航空母舰上担任独立医官时,他发现没有其他医生可供推诿了。更不妙的是,每天到舰上巡视的医疗指挥官已经对他错误连篇的诊断报告起了疑心。德马拉干脆叫人在下层船舱上挂上隔离牌,把凡是闹不清病因的病人全关在里面,他的诊断质量在短时间内立刻提高。不想没过多久,他被派往“卡育加”号做医生,那艘战舰将去前线执行任务。他决定把牌玩到底,用自己的运气和全船官兵的性命赌一把。
“卡育加”号抵达日本海的第一仗后,二十几个受重伤的士兵被抬回船上等待手术。德马拉把自己反锁在船舱里,整瓶整瓶地灌朗姆酒,祈祷上帝让船撞上一颗鱼雷沉没。当勤务兵再次敲舱门时,他快速地在胸前画了几个十字,为舱外那些不幸的小伙子和他自己祈祷。他决定从伤势最轻的士兵治起,这样考虑很有讲究:一来可以在实践中熟悉外科手术,二来伤势严重的士兵可能等不到手术就会死去。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他成了英雄。上帝对他6年掺杂着欺骗成分的宗教生涯做出了回应,醉醺醺的赛尔医生突然变得医术高超、镇定自若,连续十几台手术都极为成功。他利索地从伤员的躯体上挖出一把把弹片—有的深陷到心脏附近;他使一个濒临衰竭的肺重新恢复了功能;他修复并缝合了十几处严重的伤口。天亮后,当他走出手术室时,四周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随着战事的推进,他成功地进行了几百台大大小小的手术,甚至一边对照着《柳叶刀》杂志,一边完成了外科最复杂的肺切除手术。他在朝鲜的表现如同圣徒:在假日帮助当地建立医院和供水管道,为村民们义诊。他的事迹被很多家欧美报刊转载。在大洋彼岸,真的塞尔医生不断接到热情洋溢的来信和电话,他从报纸上读到了自己的事迹,他认出那个人似乎叫弗伦奇……
尽管“卡育加”号的全体水兵都对德马拉表示支持和同情,但他还是在1952年年末以最快的速度被踢出了海军,一无所有地重返街头。圣诞节时,他把自己的故事以1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价码。
回到美国后,他试着去儿童福利院工作。在那里,孤儿和少年犯都很喜欢他,直到他被人从杂志上认出来。
1955年,他使用琼斯这个化名,在得克萨斯州最大的亨兹维尔监狱应征当了看守。他敢于冲进暴动的犯人中间,用传教士的仁慈和摔跤手的体格使他们安静下来。两年后,他被提升为副典狱长,专门负责死刑重犯,这个史无前例的提升速度连州长都感到惊讶,亲自打电话给典狱长,询问出了什么事。后来骗局穿帮,典狱长埃里森还说:“不管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只要他能弄到合法的证件回来,我照样会让他做副典狱长。”
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德马拉为犯人们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其中就有刊载他的故事的那期《生活》杂志。当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犯人边翻那期旧杂志边打量他时,他快步回家去收拾行李。
1958年,德马拉在墨西哥做了一段时间的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一座大桥。回到美国后,他用假名做过牙医、精神分析专家,在学校教过生物学、心理学、法语和拉丁语,又先后几次进出修道院。在缅因州、马萨诸塞州甚至遥远的阿拉斯加和古巴,他都被人从那本杂志上认了出来。1960年,他的故事被拍成一部名叫《伟大的骗子》的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票房热门,他还因此参与了另外一部恐怖片的拍摄,在里面扮演一名医生。
1960年,一个认识德马拉的传记作者接到他的电话,他拒绝透露自己在哪里,只是说这一次“又把他们耍了”。自此,他成功地离开了公众视野达20年之久。
20世纪80年代,曾被他冒名顶替过的约瑟夫•塞尔医生在一间手术室里再次遇见了他。德马拉前来为临终者做忏悔,天知道他这一次叫什么名字。塞尔医生沉默地注视着手术台对面这个高大、衰老、比任何教士都更像教士的男人虔诚地完成了他的仪式,他没有任何理由揭穿这个人。
1988年,德马拉走完了疲惫、难以定论的一生,他不必再扮演什么人。
德马拉1921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他父亲曾拥有一家知名的电影公司。家道败落后,他个性中的敏感、骄傲渐渐发展为烦躁、任性。14岁时,他从中学出走,开始了漫游,先在罗德岛一家修道院待了几年,随后进了部队。
德马拉具备观察和利用制度漏洞的天赋。在部队时,他有办法逃过繁重的劳动;只要戴上一个快递员臂章,他就可以走到食堂长长队伍的前面,最先吃到热饭。军旅生活对他来说太过无聊,1941年12月4日,他偷了一张身份证开了小差。三天后的早晨,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军队开始搜捕逃兵,德马拉做了个奇怪但精明的选择:重新加入海军。
他在海军医学院完成了基础医学课程。由于没有高中学历,他只能被分配去荒岛做陆战队医务兵。面对这样的安排德马拉可不甘心,于是他偷了几份学院的档案,使用一个姓弗伦奇的医生的履历申请做军医官。军方很快给他授衔。然而,当他了解到部队还要对他进行治安审查后,就把一封遗书和军帽留在海岸上,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营地。这一年他刚满20岁,高大强壮,面相比实际年龄沉稳老练,学会了不把内心的慌乱表现出来。
德马拉对宗教抱有浓厚兴趣,离开军队后他打算直接从主教做起。他继续使用弗伦奇医生的履历,先后在26个不同教派的宗教团体里厮混过,每次都引起修道院院长或大司铎的怀疑。其中一次,他已经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神学院研究生的课程,但因为不满自己的教职,直接偷了院长的证件逃往南方。
又被几家神学院和修道院识破以后,1947年,德马拉在华盛顿再次走运,为圣马丁修道院筹建心理学系,并进入了当地的权贵阶层。这年夏天,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两次逃脱兵役把他从修道院带走。
在法庭上,德马拉运用从教会学来的动人口才向法官忏悔:6年来,宗教生活已涤清了他的心灵。在赢得战争的美国,人们相对宽容,他被判了6年监禁,最后只服了18个月刑。
德马拉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出狱后,他晚上在医院上班,白天在一所法律学校听课,但他无法容忍从系主任到旁听生的落差。1950年,他使用约瑟夫•塞尔医生的名号,前往加拿大报名参加朝鲜战争。塞尔医生确有其人,德马拉曾经复制过他全套的毕业证书和行医执照。在新布伦瑞克的加拿大皇家海军兵站,医院夜班看护德马拉用了两个小时成为海军上尉约瑟夫•塞尔。他把自己塞进一套崭新神气的镶金边蓝色制服里,无忧无虑地前往海港报到。
那将是他一生中最奇特和浪漫的年头。
在海军医院时他干得不坏。他学过基础医疗课,知道有一半的病不用治疗就能自愈;对于另外一半,他使用大量抗生素,再治不好,就把责任推给最近的一个医生。当被安排到一艘航空母舰上担任独立医官时,他发现没有其他医生可供推诿了。更不妙的是,每天到舰上巡视的医疗指挥官已经对他错误连篇的诊断报告起了疑心。德马拉干脆叫人在下层船舱上挂上隔离牌,把凡是闹不清病因的病人全关在里面,他的诊断质量在短时间内立刻提高。不想没过多久,他被派往“卡育加”号做医生,那艘战舰将去前线执行任务。他决定把牌玩到底,用自己的运气和全船官兵的性命赌一把。
“卡育加”号抵达日本海的第一仗后,二十几个受重伤的士兵被抬回船上等待手术。德马拉把自己反锁在船舱里,整瓶整瓶地灌朗姆酒,祈祷上帝让船撞上一颗鱼雷沉没。当勤务兵再次敲舱门时,他快速地在胸前画了几个十字,为舱外那些不幸的小伙子和他自己祈祷。他决定从伤势最轻的士兵治起,这样考虑很有讲究:一来可以在实践中熟悉外科手术,二来伤势严重的士兵可能等不到手术就会死去。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他成了英雄。上帝对他6年掺杂着欺骗成分的宗教生涯做出了回应,醉醺醺的赛尔医生突然变得医术高超、镇定自若,连续十几台手术都极为成功。他利索地从伤员的躯体上挖出一把把弹片—有的深陷到心脏附近;他使一个濒临衰竭的肺重新恢复了功能;他修复并缝合了十几处严重的伤口。天亮后,当他走出手术室时,四周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随着战事的推进,他成功地进行了几百台大大小小的手术,甚至一边对照着《柳叶刀》杂志,一边完成了外科最复杂的肺切除手术。他在朝鲜的表现如同圣徒:在假日帮助当地建立医院和供水管道,为村民们义诊。他的事迹被很多家欧美报刊转载。在大洋彼岸,真的塞尔医生不断接到热情洋溢的来信和电话,他从报纸上读到了自己的事迹,他认出那个人似乎叫弗伦奇……
尽管“卡育加”号的全体水兵都对德马拉表示支持和同情,但他还是在1952年年末以最快的速度被踢出了海军,一无所有地重返街头。圣诞节时,他把自己的故事以1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价码。
回到美国后,他试着去儿童福利院工作。在那里,孤儿和少年犯都很喜欢他,直到他被人从杂志上认出来。
1955年,他使用琼斯这个化名,在得克萨斯州最大的亨兹维尔监狱应征当了看守。他敢于冲进暴动的犯人中间,用传教士的仁慈和摔跤手的体格使他们安静下来。两年后,他被提升为副典狱长,专门负责死刑重犯,这个史无前例的提升速度连州长都感到惊讶,亲自打电话给典狱长,询问出了什么事。后来骗局穿帮,典狱长埃里森还说:“不管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只要他能弄到合法的证件回来,我照样会让他做副典狱长。”
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德马拉为犯人们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其中就有刊载他的故事的那期《生活》杂志。当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犯人边翻那期旧杂志边打量他时,他快步回家去收拾行李。
1958年,德马拉在墨西哥做了一段时间的总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一座大桥。回到美国后,他用假名做过牙医、精神分析专家,在学校教过生物学、心理学、法语和拉丁语,又先后几次进出修道院。在缅因州、马萨诸塞州甚至遥远的阿拉斯加和古巴,他都被人从那本杂志上认了出来。1960年,他的故事被拍成一部名叫《伟大的骗子》的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票房热门,他还因此参与了另外一部恐怖片的拍摄,在里面扮演一名医生。
1960年,一个认识德马拉的传记作者接到他的电话,他拒绝透露自己在哪里,只是说这一次“又把他们耍了”。自此,他成功地离开了公众视野达20年之久。
20世纪80年代,曾被他冒名顶替过的约瑟夫•塞尔医生在一间手术室里再次遇见了他。德马拉前来为临终者做忏悔,天知道他这一次叫什么名字。塞尔医生沉默地注视着手术台对面这个高大、衰老、比任何教士都更像教士的男人虔诚地完成了他的仪式,他没有任何理由揭穿这个人。
1988年,德马拉走完了疲惫、难以定论的一生,他不必再扮演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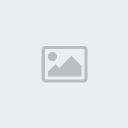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