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文/罗肇锦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文/龙应台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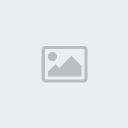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