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个局,我做局外人
这个时代鲜花盛放。
关于盛会的流水席,关于国际都会的追求,关于创富升职的成功学,无数人参与其中,成为奇葩或绿叶。
而他们是野草闲花。他们走在少人走的路上,自有暗香。他们是大时代的隐士与幽人,写生人与浅唱者,幻想家与伴奏者,流浪者与走读者。
他们主动与社会潮流保持距离。你可以视其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可以说他们拧巴。但正是有了他们映衬,你更能读懂这个时代。
“名利”不是大时代的奢侈品,“幸福”才是;“成功”不是个人魅力的源泉,“真我”才是。奋力挤进大时代的主流圈子做时代的弄潮儿是一种活法,在大时代边上做一个我自有我梦的自在者是千万种活法。
时代是个局,做个局外人,也不错。
你和时代合唱,我和自己独吟
时代边上的人与时代中心的人最大的不同,不在所处的位置,而在所持的态度。他们离时代的中心越远,离自己的内心就越近。
文/黄俊杰
他是拿过3枚金牌的奥运冠军;他是中国96万个千万富翁中的一人;他是微博粉丝超过100万的知道分子;他是超过1亿人收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活在时代的中心。
我是每天9点上班的宅男;我是全国排名20位之后大学的毕业生;我是在24岁时解散乐团去当白领的人;我是年近三十依然无房无车的贫下中产——我活在时代的每一处。
你是到云南开客栈的弃业家;你是隐居山村的博士后;你是外表平凡的民间高手;你是为自我而活的人;你是人满为患的饭局中从来默默无语的一个——你活在时代的边境。
若然把时代比喻成一场秀,有人愿意登台表演,有人根本不想入场;如果把时代比喻成一个国度,有人活跃在中心的名利场,有人则游荡于精神的边境。直至有一天我们发现,时代边上的人与时代中心的人最大的不同,原来不在位置,而在态度——你不是被挤到时代边缘的人,而是主动选择来到时代边上的人;你离中心越远,离内心就越近。
大时代边上的人物肖像
“我很懒,缺乏耐性和毅力。我想减肥增强体质,但我跑步只坚持了两天;我抽烟,我知道这是危害健康的表现,但我戒不了;我任性,父母也拿我没办法;我直来直去,得罪人成了家常便饭;我爱发脾气,不懂得控制情绪,谁学我都会倒霉。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我自信又自卑,矛盾得要命。”
王菲的这句话,说的好像是我们自己。我们随时代大流顺流而下,以致变成今日的样子——我们留过分头、爱过港产片、学过席殊、相信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迷信过重点大学、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焦虑过房子的首期;我们为集体无意识所裹挟,像“每个人”一样生活,直至身躯日渐发福,才为《老男孩》中所唱的一句“未来在哪里平凡”而叹息;我们同样饱尝过生活的不安、痛苦与焦灼,却从未想过离开庸常的生活。
这样的我们,每天都关注着时代中心的人物。他们努力奋斗、意志坚定、经历坎坷,最终受人拥戴、名利双收,简直就是成功学的范例与人生的最佳意淫对象。但这样的人生并非全无代价,当已身为时代中心人物的季羡林回忆80年来的人生,面对“若让自己重来一次要怎么样”的自问,依然说了反话:“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在前往时代中央舞台的路途中,名气大不一定代表才华高、财富多不一定代表活得好、学识高不一定代表不会精神空虚,多数人称颂不一定代表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不一定代表讲出真理——他们活得像一部成功学,未必就懂得什么是幸福;他们活得像一句广告,但未必就是真实的自己。
此刻,我们终于发现还有一种“时代边上的人”。你与他同样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但时代中心的人追求的是比别人更强更好,你追求的却是更像一个人本身;你与他同样拥有自己的原则,但时代中心的人有着合理、优选、标准、一致的“工业标准”,你只是想活出真实的自己。
人有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不同的自己。大时代边上的人,内心强大,甘于静止,自得其乐,不涉主流;不刻意与别人一致,也不故意与别人不同;能忽视他人目光而自持,放弃追随主流价值而自省,远离名利场而自新;还有着如同加缪在《局外人》中赋予默尔索的美德——“不会耍花招”、“拒绝说谎”、“坦诚、光明正大、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
大时代边上的人,首先是一个“人”。
与时代相处的方式
“这部词典将是对人们赞同的一切的历史性颂扬。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世人在福楼拜的遗物中发现了《庸见词典》——但基本上,福楼拜写这个是为了嘲笑“资产者”的愚蠢无知。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欲望时代,多数派的庸见早已对我们潜移默化,成为我们“想得却不可得”的一系列人生追求:时尚的庸见让我们即使变成卡奴也要买爱马仕;丈母娘的庸见让我们即使变成房奴也要有个固定地址;成功学的庸见让我们即使做牛做马也要贴上个贫下中产阶级标志;假道学的庸见让明明不关心人类只关心林妹妹的我们,非要满嘴跑着似是而非的“Pussy价值”。
在地铺上睡过11年的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有名言:“人有三个姿势,爬着、蹲着、跪着,这三种姿势都可能选,在创业的时候想站着很难。更多的时候是爬着,这是心态上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我们往往先被生活和环境给压缩到零,要从零像手风琴一样拉出来才有旋律。”但是,在《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一句台词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海:“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我们自问:是否要为成功跪着?要将自己压缩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得到认可?往名利场中心挤去,真是一个好主意?
“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风,遍体鳞伤,才知道自己是草。”这是《艋舺》的台词。拒绝时代是有难度的事,不是每个人都有安然活在大时代边上的才华——韩寒曾有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参加演出等“12不”,但我们依然看过他为华硕电脑拍的“爱梦想,做自己,我是韩寒”,以及
“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的标榜自我的广告——尽管他曾为涉及商业活动而“谢罪大家”:“我已经很多天都失眠不安,这么多年难得和大家交流一次还要染上商业色彩,真的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时代中心有一张摆放着声名、金钱、成功与性的欲望榜,有时要让我们用珍贵之物去交换——《非诚勿扰》有博士安田因女嘉宾在假设如何花1000万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想法而单身离场,让我们记住了哈佛大学入门写有的校训:“进入哈佛是为了增长知识,离开哈佛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托富勒说:“眼睛能目睹一切,唯独看不见自己。”在众声喧嚣、目不暇接的时代,我们不再单纯,遗忘信仰,远离精神世界,逐渐连做逼真的自己都做不到。
有人按自己的方法来与时代相处。木子美在微博上的名字叫“不加V”,她曾这样说过:“以我的聪明才智,本能过得好10倍,我因太爱自由,失去了10之9。可我还是过得不错啊。唯一有用的,就是告诉大家,做真实的自己未必活不下去。”
我们需要找到与这个时代相处的方式。也许,时代中心与时代边上的人应该各司其职,正如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改变时代的重担,但每个人都有权在时代允许的游戏规则之内活出真实自我——如果从来没有试过大声说出自己的心声,便应该尝试在大时代边上找到缺席的自己,应该尝试让内心比时代更强大。
大时代边上的人是小写的“人”。唯有社会的多元与宽容,才能让“大时代边上”变成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1932年3月,写过《我们》的扎米亚京在和一个记者谈话中说过:“人们给我讲过波斯的一个关于公鸡的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入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这只公鸡的头。”大时代边上的人物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应是社会的进步;即使你未必想过要改变时代,未必将所谓的重大使命加于自身,但是,做好一个时代边上的自己,也许亦是推动时代的一种方式。哪怕,这并不是你的本意。
这是一个当局者迷、旁观者也看不清的时代。时代如同一条奔流之河,我们都是里面的游鱼。偶然有鱼跃出水面,窥探了前面的一段河面,却总有些没有顺流而下,反而往一边游去。
大时代边上的补白
善待异见,是时代最大的进步
那些自我边缘化者,不追求站在大时代的舞台中央,不追随主流价值,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他们不是被动地被挤压到时代边上,他们只想做真实的自我,按自我的方式生活,不想被一勺烩罢了。
文/肖锋
混沌理论认为,个体不被整体改变必需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自身足够强大;第二,坚持得足够久。
强大的个体改变整体,万物以至人类得以进化。强大的个体不一定是领袖,他们可以是异类,比如第一只站立行走的猴子。
多数人的选择,可能是多数人的暴力。假如一个浮躁的消费主义时代将人类引向毁灭,那么异类就是一种救赎。他们或许以不情愿的方式在大时代边上留下补白,提醒人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时代不可缺少的补白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因为人心坏了,大好形势也难持久。
在海内外造势者营造的“大好形势”之下,有人奋力攀爬,有人出逃,有人选择自我边缘化。
那些自我边缘化者,不追求站在大时代的舞台中央位置,不追随主流价值,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他们不是被动地被挤压到时代边上,他们只想做真实的自我,按自我的方式生活。因为他们懂得,成功而不快乐是最大的失败。
造势者称,中国中产阶层改写奢侈品规则:穿Prada的人民“月收入万元以上;开着奥迪A4轿车;住着温哥华森林或远洋新干线等明星楼盘;使用IBM ThinkPad或苹果笔记本电脑,苹果手机;经常出入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五星级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他们都习惯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他们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非”。他们叫“中产阶层”。
麦卡锡的这份中国奢侈品报告认为,中产阶层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处于全球坐二望一的位置。正是这种追求,让中国人无论是生活品质还是时尚品位都更密切地与世界接轨,甚至在某些方面引领世界。
对照现实,海外咨询机构对中国现实的描述往往很穿越。中国当下的现实恰恰中产塌陷。
那些跋扈者,为什么要通过炫富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而招致民众和传媒的批评呢?巨富者得不到社会声望,甚至成过街老鼠,所以只有依赖物质标签了。在中国,成功者或不成功者,心底都有不同意味的失败感。
要清醒而独立地活着,需要强大的内心。
既然打不过他们,那就成为他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抗拒成为他们。
有人追求成功、荣耀、功成名就,有人选择自我边缘化。自我边缘化是人类的一个永恒主题。但先要区分真淡定与假淡定。李白“皇帝呼来不上船”是矫情,假如许个一官半职就会毁了诗仙。孟浩然“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是真隐居,“何必先贤传,惟称庞德公”,他体味到了远避红尘的乐趣。
八大山人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自知性僻难谐俗,且喜身闲不属人。八大山人的书画拍卖单价超过了千万亿万元,其故居常有高官名流来拜。这个自我边缘化的僧人画师,假如当时选择红尘成功,还会有今日拜者云集吗?
历史证明,那些选择自在、自由、自得的人,那些不在乎影响主流的人,最终都影响了未来主流,成为那个时代的不可缺少的补白。
为什么是“在时代的边上”?
无论盛世、衰世,都出陶渊明。不管乞丐、皇帝,都想过出世。清顺治放着江山不坐逃遁空山。明木匠皇帝,放着朝政不理而精于木活。有人小隐隐于野,有人大隐隐于朝。人人都有一点《越狱》情结,但未必都去挖地道。
关于逃,佛经有个经典故事:有一个犯人判了无期徒刑,想逃出监牢,就与同牢的小偷商量。他们慢慢挖地洞,一天挖一点,最后成功了。等到小偷逃走,这个犯人就把地洞盖好,他自己呢,反而跟看守们变成好朋友。家里送来好吃的,大家一起吃,好玩的一起玩,后来与看守无话不谈,大家放心他,晓得他不想逃。有一天家里又送来酒肉,他就请看守一起来庆祝,等到看守酒喝醉了,他就从看守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打开自己的手铐脚镣,穿上看守的制服,把牢门打开,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而那个小偷,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个地洞逃出来,还很可怜地东躲西躲,身逃出来可心还在牢里呢。而那个判无期的,因为跟看守都变成朋友,却彻底地逃出来了。
逃不在乎方式、不在乎逃往何处。吕洞宾在庐山仙人洞题有诗:“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所以,有人日理万机心却早已逃了出去;有人身在仙境,心却在生意场中。
逃进深山老林、逃去丽江大理,你以为就逃脱了吗?
为什么是在时代的边上?与红尘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与主流保持刻意的距离,非暴力不合作,正是价值所在。你别想把我变成你的一员,我不想成为你的一部分。否则大家一勺烩了,全完蛋。那些被绞进事业、职场、官场的绞肉机里的人们,不能自拔,最终成为大酱缸的一部分。这好吗?
中国有个三千年来的权力磁场,好比强大的风洞,将一切卷入其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进化论需要特立独行者,大自然需要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多元性,乃进化之本。同样,生活方式多样性亦是人类幸福之源。
选择不合作,选择不跟风,活出来让你们看看。每个人都有权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就不会扎堆儿,就不会一勺烩。什么时候新浪微博上尽在讨论过小日子了,那中国才算进步了。什么时候《新周刊》变成纯讨论生活方式的杂志了,那就说明中国人进入舒坦状态了。
闲时,你可以选择做个酱油男:爱潜水,爱冒泡,只发帖,不加V。有事去散步,无事看风景。你做你的采访,我做我的俯卧撑。我不是谁的炮灰,我没有凶器,只有一鼠标。我只代表我自己。每日飘过无数帖,偶尔喊上一两声。我是地球一板砖。
为什么要给异类空间?
表面看,中国有本《花花公子》,叫《男人装》。可你知道的,上世纪60年代的《花花公子》会偶露锋芒做一期反战专题。《男人装》绝不会的。中国更不会有的是《滚石》。同样是青年运动,中国的60年代与西方完全是两码事,就像大串连与伍德斯托克是两码事一样。
伍德斯托克的嬉皮士们有意识地远离主流社会,以一种不融于主流的生活方式,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叛逆。奇装异服、留长发、蓄长须、吸大麻、听爵士乐、闹群居等只是表象而已。有人要在当今中国复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就妄想了。
Do your own things,因为不爽,所以独行。人生的目的也不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人生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人生是重新发现。
16岁那年,乔布斯留着齐肩长发宣布正式成为嬉皮士的一员,并结识了生命中第一个女孩,然后喝酒、吸大麻:“有一天,我们特意到一块麦田吸***,突然间,我感觉整块麦田都在演奏巴赫的乐曲。那一刻我非常兴奋,感觉自己就好像在指挥交响乐队演出。”1974年乔布斯“光着脚、穿着破烂衣服”来到印度朝圣:“加利福尼亚嬉皮士的贫穷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印度的贫穷则是命运。”我们不知道大麻和印度朝圣与苹果公司的关系,但反叛的基因一定植入了乔布斯的每一款产品。你们是不是很受用?
另一位嬉皮士资本家是理查德•布兰森,他打造的传奇virgin商业帝国一点都不传奇,因为他只是代言了年轻世代的想法并满足他们罢了。
当某一事物占据主流,老朽的过程就开始了。政治上叫寡头,经济上叫垄断。中东革命的实质,不是你***了多少,是因为你在位太久,太老朽了。反垄断法的实质,表面是制裁垄断,实质上也是你在位太久,不利于充分竞争,让新生事物没有生长空间。
而作为嬉皮士的乔布斯们和布兰森们则具备回到原点的反叛意识与反思精神:“反对强迫消费,这样只会导致环境恶化;反对被动接受,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为什么有时我们都是嬉皮士》)。他们是60年代的一代,他们是滚石的一代,他们唱着《答案在风中》,他们终于修成正果,成为新乐公司的CEO或国际组织的领袖。
宽容异类,善待异见,就是时代最大的进步。数字出版已能做到个性化定制,出版社为某个特定客户只出一本书。有一天,人们希望也能定制属于个人的生活,只要代价不太高。当社会的长尾理论盛行,异类将成为常态。
为异类留有空间,为物种留有多样性,因为说不定哪天他们就是幸存者或拯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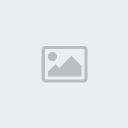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