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我向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邯郸学步,来写我心中对教育的疑惑和痛苦。本文所谓的“好学生”并非指高考出色的“考生”,而是指大学里面以探索问题为志业的学生。当下,从小学到高中模制出来的孩子多是“考生”,是以考试为业的学生。好学生当不以考试为业,而是以学问为业,以问题的探索为业。浙江大学一位教授常年带学生读书,每个毕业季都要读韦伯的“以学术为业”这一名篇,以送别读书班的学生。好学生当然并非一定要以狭义的学术为职业,但好学生须以广义的学术即学问和问题为志业。我想要问的是,这样的一群以学问和问题为业的人都去哪儿了?令人忧虑的或许是,这样的人正在各个教育阶段消失,尤其明显的是在大学这至关重要的学习阶段消失。
好学生都去哪儿去了?记得媒体讨论过现在大学生暮气深重的话题。大家好像也都为大学生的暮气,与之相关地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焦虑。然而也许有人会质问我:“你凭什么说今天的学生暮气深重?”是啊,他们的见识比我这样的老朽广、门道比我清、考分远比我高。何来暮气深重一说?不过,本文所说的“暮气”至少有一个核心含义,就是缺乏理想的激 情。
一个暮气深重的人,一群暮气深重的大学生,指的是缺乏理想之***的年轻人。又有什么能够清除暮气?唯有致力于问题的不懈探索!今天的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面向未知世界的想象。他们大多生活在一个被安排的世界里,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世界里,大多也就失去了对最为切己相关的“命运”(即问题)的好奇感。“问题”是一个人的命运,也会是一个国家的国运。对“问题”的不竭探索造成薪火相传的精神,而失去面向“问题”存在的勇气就是所谓的暮气,它表现在只关心直接的、眼前的利益。满眼所及,均皆如此。从小学到高中,学生的暮气深重表现在唯成绩至上;在大学里,学生的暮气表现在唯“钱途无限”为其职业追求。好学生都去哪儿了,实则是理想的激 情都去哪儿了。
如果只是学生丧失了理想的激 情,如果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理想的激 情的校园里面,还有可能实现“肖申克的救赎”。可怕的是大学也在失去“唯学问”为是非的理想的激 情。当大学为各种评审制度钳制的时候,大学的激 情就已经被削弱;当各种规章制度变成教师们搔断白发都不得其解的难题时,大学的激 情在教师身上也就被削弱;当学生仅为绩点学习时,大学作为象牙塔就已经轰然倒塌。面向学问的激 情是大学精神的根源;大学之谓象牙塔,即在于此。“好”大学必是愚拙的,这样的大学必有不动心的淡定。也唯有这样的大学,才能造成教师的不动心和一群不动心的学生;一群不以机巧为学问的教师,才能养成一群不以取巧为悦感的学生。这样的不动心,才能真正养成精神传统。精神传统乃是保守的东西,一个开放社会恰恰需要至为保守的精神,就是对于道义、自由、公正、友善和慷慨等等德性的看护和坚守,就是对于宏大理念的信任,也是对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理想的坚持。好学生都去哪儿了?当大学念念于就业率,念念于校友富豪榜及捐赠数额时,肖申克监狱中“安迪”的理想的激 情就不再有丝毫的光芒。
好学生都去哪儿了?当我们这样追问时,一定要记得在今天器物对人钳制的可怕程度绝不逊色于思想的钳制,因为受器物钳制的人通常很难再唤起反思意识。而能够挣脱器物钳制的学生必是好学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地保守着自己。她不会以嫁一个外国人从外国人身上取得国籍而更具幸福感;他不会为自己职业的低微卑微觉得人格受损。他们接纳的是自由的广度和尊严的深度,就如一棵树不断地汲向更深的泉源。
我犹记得一位学生,毕业时她写信告诉我要去往非洲做一年的NGO,然后看看以后是否做非洲研究。这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一种人之为人的勇气。我也记得一位学生,他大一属于人文大类,然而当他发现对建工更感兴趣时,就凭着优秀的学业转入建工学院。在发现原来所学远不能够完成新学业时,却更加斗志昂扬。画图技艺急需提高,那好,就在假期和业余时间加强训练;物理数学知识有待深造,那好,就珍惜每秒时光。好几次在大学校园里碰到他都睡眼惺忪,说是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到处游历,每到一处必去瞻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不唯建筑为材料工程的事业。他花许多时间在精神形式上,去台湾就到寺庙打坐参禅,去美国也学着在教堂做礼拜,到藏边就钻山沟与少数民族原住民生活。毕业时找到了一份高薪酬的工作,但他觉得自己还没学够,就选择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这样的好学生都去哪儿了?这样忠于自己、忠于苏格拉底所说的内心的神谕的好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凤毛麟角?
为此一哭!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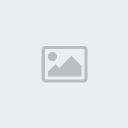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