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太怕不得奖” ——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人、中国片(2014威尼斯电影节)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2014-09-11 19:27:54
 《天 浴》之后,陈冲就没有再当导演。也有过想拍的东西,但给人看了之后,对方的回答都是:太高端、不商业。陈冲也为柏林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担任过评委。在她看来,能够让全球观众接受的“全球故事”,都胜在“对人心、对某一种人性的挖掘”。(CFP/图)
《天 浴》之后,陈冲就没有再当导演。也有过想拍的东西,但给人看了之后,对方的回答都是:太高端、不商业。陈冲也为柏林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担任过评委。在她看来,能够让全球观众接受的“全球故事”,都胜在“对人心、对某一种人性的挖掘”。(CFP/图)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同时,来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少了。电影节主席巴贝拉认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去拍适合本土观众口味的电影,放弃了国际市场。
“威尼斯电影节是中国电影的老朋友。”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贝拉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老朋友”遇到了新问题。“在中国寻找一部符合国际市场口味的电影,现在变得很难,越来越多中国的电影人放弃了国际市场,只拍摄适合本土观众口味的影片。”这是巴贝拉的观察。
2013年,巴贝拉到中国选片,几乎找不到一部合乎金狮奖参赛水准的影片,最后只有文晏的导演处女作《水印街》入围了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
2012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年收入达170.7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3年,中国年度票房收入更达到217亿元。而为这个票房作出贡献的中国电影,在业内人士看来,几乎都是“走不出去”的本土商业片。
王小帅新片《闯入者》是金狮奖竞赛单元惟一的华语片,虽无斩获,仍被《综艺》、《好莱坞报道》等媒体评论为“够水准”。《综艺》杂志评论,《闯入者》以及展映片《亲爱的》、《黄金时代》,只是中国电影的“偶然”:“中国国内讨巧的商业电影票房如此之高,已经威胁到符合国际市场口味的艺术电影的产量。”
“大家都在说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好,但我们看到,只有一部中国电影出现在主竞赛单元。中国电影究竟为世界电影贡献了什么?”电影节开幕式上,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提问咄咄逼人。她点名让许鞍华回答。许鞍华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评委会主席,另两位华人女性,演员陈冲与导演、制片人文晏,则分别担任金狮奖评委和“未来之狮”最佳处女作奖单元的评委。她们成了电影节上瞩目的“中国”形象。
许鞍华停顿了两秒,说:“我们现在拍电影的确有很多钱,但是钱不能说明一切。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我们也在尽力。”
王小帅赋予了老邓非常强势的一面。她曾经加害过别人,只是为了让小儿子能出生在北京,让家庭变得更好。但是社会的变化她无法掌控,几个孩子并不如她所愿,她试图强势地控制,但并没有成功。“这种强势的控制欲从哪里来?追溯到过去,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也曾经被强势地控制过。”1966年出生的王小帅说。
片名“闯入者”在翻译成英文时,没有直译,而是翻译成“红色失忆(Red Amnesia)”,突出“文革”伤痕的一面。
王小帅试图向西方观众解释“文革”伤痕和现实的关联。“我通过我的父母辈看到,他们在晚年积极地想找回自己,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得让他们找不着了。我们的历史并没有简简单单地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是我们精神里受到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历史造就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以及带有红色印记的中国。现在很多人提反思,就是为了让未来中国在走向更强大的时候,增加多一些理性,不要再去重复让很多人受到伤害,很多人的自我受到损伤的那个过去。”
1986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来中国拍摄《末代皇帝》,还到北京电影学院演讲。那时王小帅还是导演系的一名学生,“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到中国来拍中国过去皇帝的故事,这给我很大的刺激——电影做到一定的高度,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拍完皇宫,还拍到了溥仪变成老百姓以后的现实生活。王小帅很受启发:要拍一个中国的,同时也是“国际化”的故事,“除了传递文化符号,还要传递出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
电影《闯入者》尾声,老邓回到当年当“知青”的贵州小县城,寻找自己的过去。她走过一排破旧的厂区老砖房,《山楂树》的音乐响起,记者前排,几位法国、意大利的中年观众,跟着小声哼起了旋律。
“看《闯入者》需要一点耐心和近距离的关注,但是这部表演上佳的电影会领我们一窥中国一段复杂的历史。那一代人与过去的迷茫关系,导致了他们身处现代中国社会的尴尬处境。”《好莱坞报道》这样评论。
陈冲是最早和国际一流导演打交道的中国演员之一。1986年,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时,她在片中演了女主角婉容。有场戏,她在小皇帝面前更衣,一不小心衣服滑下去出现了一个裸露镜头,为此还和贝托鲁奇起了些小矛盾,她坚持要跟贝托鲁奇补签一个合同,保证这场戏不能放。
《末代皇帝》夺得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九项大奖,也让陈冲和“溥仪”尊龙走上了奥斯卡颁奖台。与贝托鲁奇等西方导演合作,陈冲很早就了解到,“讲人性故事很重要”。
陈冲近年常和“艺术电影”打交道。2007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陈冲演“林大夫”,漂亮风骚,就像一个被压抑太久,忽然性苏醒的一个女性符号,有点亢奋,又有点病态。
2008年,贾樟柯拍《二十四城记》,陈冲甘愿“跑龙套”,演一个从上海分配到成都国营老厂的“厂花”。“我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他记录了我们的时代,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人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他在关注应该得到关注而没有受关注的人、人生以及命运。”陈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2年,文艺片导演李玉拍摄《二次曝光》,陈冲又是“跑龙套”,演一个整形医生。她参演的理由很简单:“李玉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个性,我挺想认识她、了解她,看她工作。”
陈冲在1998年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天 浴》。《天 浴》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讲“文革”末期,四川女知青文秀为了回城,出卖自己的肉体,最终甚至搭上性命的悲惨故事。影片在国内被禁映,但陈冲凭此片获得台湾第35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之后,陈冲没有再当导演。有时有了想拍的东西,但给一两个人看了后,对方的回答都是“太高端”、“不商业”。
“我不一定特别合适现在的市场。”陈冲显得有些无奈,“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的生活经历很平安,没有经过大的运动。经济上的发展,剥夺了思想上的探索,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努力挣钱,而不鼓励你去深刻地思考。”
陈冲还曾为柏林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担任评委。在她看来,能够让全球观众接受的“全球故事”,都胜在“对人心、对某一种人性的挖掘”。
“人们毕竟喜欢皆大欢喜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会挑战你先前的某一种感觉,它让你更深刻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人类的命运,有它的意义和必要性。”陈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她看到一些竞赛影片,“在某种压力下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把整部电影所毁掉了”。
文晏是电影《白日焰火》的制片人。2014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及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国内票房超过一亿。《白日焰火》很快被赋予了“文艺片与商业结合的范本”等诸多标签。
2013年,文晏在威尼斯电影节的身份是导演。她的处女作《水印街》入围第70届威尼斯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水印街》讲述一对中国城市年轻人的忧伤爱情,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场意外卷入的风波而被打乱。文晏希望探讨一种充满悖论的生存状态:“比如现代科技对我们隐私的介入,它既可以保护你,又可以伤害你。”
《水印街》投资250万,拍摄历时一个月。片中的年轻人不再来自中国的乡村或者城乡接合部,而是来自城市,听着和西方一样的流行音乐,过着和他们相似的生活。在威尼斯首映时,一家意大利电影杂志评价说,这部电影让他们想起了安东尼奥尼电影《放大》,都是关于真实与虚幻的一种变化。
“中国在变化,北京可能没有那么异域风情了,都是一样的高楼大厦了。怎么在这样的景象中拍出中国的质感来?”文晏说,这是她常常思考的问题。
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很多西方电影也会做。但如果一个作者平日养尊处优,对底层生活完全不在意,突然之间就要写一个残疾人,一个底层小人物,“我认为那是不真诚的,他拍出来的电影一定会有问题。”文晏说,比利时著名导演达内兄弟,他们影片的主人公是煤矿工人、木匠、清洁女工、失业者,但他们的方法是真正走到那些人当中,没有俯视,也没有施舍。
《黄金时代》讲述了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女作家萧红的短暂一生,以及她与作家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感情。三小时的影片中,有三十多位民国年代的文人出场。他们对着镜头,用自己的记忆和印象,为观众拼凑起一个萧红。
要悉数将三十多人对号入座,即使对中国观众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鞍华解释,她执意要尝试一种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悬案,我们没有说给你们看一些什么定案的东西,只是根据一手资料,她自己写的、朋友写的,整理出来。有疑案,就告诉你是个疑案。”
从观众反应来看,这并不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实验。“许鞍华的野心很大,她想在这部电影里放进很多大格局,那个文人辈出的民国时代,还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政治性和个人选择的冲突,重新树立一种传记片的标准……但恰恰是这些野心束缚了她,造成了《黄金时代》的问题。”《综艺》杂志这样评论。
2011年,许鞍华在威尼斯电影节展映的影片《桃姐》,获得来自西方观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桃姐这位温柔的、有质感的,具有低调的人文精神的女性,也是许鞍华身上完美的电影标签。”
许鞍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履行“地平线”单元评委主席职责。有别于金狮奖,地平线单元重点鼓励电影的实验和创新,以捕捉世界电影未来的潮流和趋向。
“很多国家的名字我都不认得,但很多电影拍得非常好。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都是新的导演,他们去西方的电影学院学习,然后回他们国家自己拍戏。”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这些影片中,许鞍华看到如今世界艺术电影的三股“潮流”:一类是反映现代年轻人的虚无,“割手、吸毒、流浪不回家,然后特别理直气壮”;一类她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故事,比如阿拉伯地区战争的题材,或者在中东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一个老妇人独自生活的故事;还有一类,就是传统的批判题材,比如控诉某种制度。
最容易打动她的,首先是那些批判性的题材,“最后那个判断是什么不重要,呈现最重要,如果你能投入他所呈现的东西,你就受到教育了。”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在许鞍华看来,是一次学习世界电影怎么讲故事的过程。“学习人家的东西,不一定是技术,而是文化上的东西——他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太紧张、太害怕了,怕我们的片子不得奖,就没有时间去欣赏别人的电影。但这才是电影节最重要的。”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2014-09-11 19:27:54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同时,来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少了。电影节主席巴贝拉认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去拍适合本土观众口味的电影,放弃了国际市场。
“威尼斯电影节是中国电影的老朋友。”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贝拉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老朋友”遇到了新问题。“在中国寻找一部符合国际市场口味的电影,现在变得很难,越来越多中国的电影人放弃了国际市场,只拍摄适合本土观众口味的影片。”这是巴贝拉的观察。
2013年,巴贝拉到中国选片,几乎找不到一部合乎金狮奖参赛水准的影片,最后只有文晏的导演处女作《水印街》入围了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
2012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年收入达170.7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3年,中国年度票房收入更达到217亿元。而为这个票房作出贡献的中国电影,在业内人士看来,几乎都是“走不出去”的本土商业片。
王小帅新片《闯入者》是金狮奖竞赛单元惟一的华语片,虽无斩获,仍被《综艺》、《好莱坞报道》等媒体评论为“够水准”。《综艺》杂志评论,《闯入者》以及展映片《亲爱的》、《黄金时代》,只是中国电影的“偶然”:“中国国内讨巧的商业电影票房如此之高,已经威胁到符合国际市场口味的艺术电影的产量。”
“大家都在说中国电影市场如何好,但我们看到,只有一部中国电影出现在主竞赛单元。中国电影究竟为世界电影贡献了什么?”电影节开幕式上,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提问咄咄逼人。她点名让许鞍华回答。许鞍华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评委会主席,另两位华人女性,演员陈冲与导演、制片人文晏,则分别担任金狮奖评委和“未来之狮”最佳处女作奖单元的评委。她们成了电影节上瞩目的“中国”形象。
许鞍华停顿了两秒,说:“我们现在拍电影的确有很多钱,但是钱不能说明一切。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我们也在尽力。”
历史并没有简简单单地过去
《闯入者》的故事发生在现代的北京。LV、爱马仕、苹果电脑……这些名牌形象不断在电影中出现,反映中国人的“好日子”。这样的好日子里,吕中扮演的空巢老人老邓却反复陷入困境。她常常不打招呼就“闯入”两个儿子的生活,与大儿媳不睦,小儿子的同性恋,也让她不知如何面对。独自在家时,老邓常常受到一个无声电话的骚扰,还有一个16岁的男孩,像幽灵一样跟着她。王小帅赋予了老邓非常强势的一面。她曾经加害过别人,只是为了让小儿子能出生在北京,让家庭变得更好。但是社会的变化她无法掌控,几个孩子并不如她所愿,她试图强势地控制,但并没有成功。“这种强势的控制欲从哪里来?追溯到过去,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也曾经被强势地控制过。”1966年出生的王小帅说。
片名“闯入者”在翻译成英文时,没有直译,而是翻译成“红色失忆(Red Amnesia)”,突出“文革”伤痕的一面。
王小帅试图向西方观众解释“文革”伤痕和现实的关联。“我通过我的父母辈看到,他们在晚年积极地想找回自己,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得让他们找不着了。我们的历史并没有简简单单地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是我们精神里受到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历史造就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以及带有红色印记的中国。现在很多人提反思,就是为了让未来中国在走向更强大的时候,增加多一些理性,不要再去重复让很多人受到伤害,很多人的自我受到损伤的那个过去。”
1986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来中国拍摄《末代皇帝》,还到北京电影学院演讲。那时王小帅还是导演系的一名学生,“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到中国来拍中国过去皇帝的故事,这给我很大的刺激——电影做到一定的高度,能够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拍完皇宫,还拍到了溥仪变成老百姓以后的现实生活。王小帅很受启发:要拍一个中国的,同时也是“国际化”的故事,“除了传递文化符号,还要传递出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
电影《闯入者》尾声,老邓回到当年当“知青”的贵州小县城,寻找自己的过去。她走过一排破旧的厂区老砖房,《山楂树》的音乐响起,记者前排,几位法国、意大利的中年观众,跟着小声哼起了旋律。
“看《闯入者》需要一点耐心和近距离的关注,但是这部表演上佳的电影会领我们一窥中国一段复杂的历史。那一代人与过去的迷茫关系,导致了他们身处现代中国社会的尴尬处境。”《好莱坞报道》这样评论。
“我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市场”
《亲爱的》在威尼斯首映,评委陈冲悄悄进了剧院。“它打动了我。”看完影片,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冲是最早和国际一流导演打交道的中国演员之一。1986年,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时,她在片中演了女主角婉容。有场戏,她在小皇帝面前更衣,一不小心衣服滑下去出现了一个裸露镜头,为此还和贝托鲁奇起了些小矛盾,她坚持要跟贝托鲁奇补签一个合同,保证这场戏不能放。
《末代皇帝》夺得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九项大奖,也让陈冲和“溥仪”尊龙走上了奥斯卡颁奖台。与贝托鲁奇等西方导演合作,陈冲很早就了解到,“讲人性故事很重要”。
陈冲近年常和“艺术电影”打交道。2007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陈冲演“林大夫”,漂亮风骚,就像一个被压抑太久,忽然性苏醒的一个女性符号,有点亢奋,又有点病态。
2008年,贾樟柯拍《二十四城记》,陈冲甘愿“跑龙套”,演一个从上海分配到成都国营老厂的“厂花”。“我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他记录了我们的时代,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人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他在关注应该得到关注而没有受关注的人、人生以及命运。”陈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2年,文艺片导演李玉拍摄《二次曝光》,陈冲又是“跑龙套”,演一个整形医生。她参演的理由很简单:“李玉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个性,我挺想认识她、了解她,看她工作。”
陈冲在1998年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天 浴》。《天 浴》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讲“文革”末期,四川女知青文秀为了回城,出卖自己的肉体,最终甚至搭上性命的悲惨故事。影片在国内被禁映,但陈冲凭此片获得台湾第35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之后,陈冲没有再当导演。有时有了想拍的东西,但给一两个人看了后,对方的回答都是“太高端”、“不商业”。
“我不一定特别合适现在的市场。”陈冲显得有些无奈,“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的生活经历很平安,没有经过大的运动。经济上的发展,剥夺了思想上的探索,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努力挣钱,而不鼓励你去深刻地思考。”
陈冲还曾为柏林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担任评委。在她看来,能够让全球观众接受的“全球故事”,都胜在“对人心、对某一种人性的挖掘”。
“人们毕竟喜欢皆大欢喜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会挑战你先前的某一种感觉,它让你更深刻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人类的命运,有它的意义和必要性。”陈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威尼斯电影节,她看到一些竞赛影片,“在某种压力下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把整部电影所毁掉了”。
一样的高楼大厦,怎样拍出中国质感
文晏的评委工作被切割成工整的几块:每天看两三部电影,每过两三天,评委们聚在一起讨论一次,直到最后一天,再整体做一个决定。“凡是那种一看就特别计算的电影,我们一般都不太会喜欢。你看不到才华,看不到生命力,只有各种担心。好的东西还真的就是个性化和发自内心的。”她说。文晏是电影《白日焰火》的制片人。2014年,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及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国内票房超过一亿。《白日焰火》很快被赋予了“文艺片与商业结合的范本”等诸多标签。
2013年,文晏在威尼斯电影节的身份是导演。她的处女作《水印街》入围第70届威尼斯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水印街》讲述一对中国城市年轻人的忧伤爱情,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场意外卷入的风波而被打乱。文晏希望探讨一种充满悖论的生存状态:“比如现代科技对我们隐私的介入,它既可以保护你,又可以伤害你。”
《水印街》投资250万,拍摄历时一个月。片中的年轻人不再来自中国的乡村或者城乡接合部,而是来自城市,听着和西方一样的流行音乐,过着和他们相似的生活。在威尼斯首映时,一家意大利电影杂志评价说,这部电影让他们想起了安东尼奥尼电影《放大》,都是关于真实与虚幻的一种变化。
“中国在变化,北京可能没有那么异域风情了,都是一样的高楼大厦了。怎么在这样的景象中拍出中国的质感来?”文晏说,这是她常常思考的问题。
关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很多西方电影也会做。但如果一个作者平日养尊处优,对底层生活完全不在意,突然之间就要写一个残疾人,一个底层小人物,“我认为那是不真诚的,他拍出来的电影一定会有问题。”文晏说,比利时著名导演达内兄弟,他们影片的主人公是煤矿工人、木匠、清洁女工、失业者,但他们的方法是真正走到那些人当中,没有俯视,也没有施舍。
艺术电影的三股潮流
2014年9月6日,许鞍华的萧红传记片《黄金时代》为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拉下帷幕。《黄金时代》讲述了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女作家萧红的短暂一生,以及她与作家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感情。三小时的影片中,有三十多位民国年代的文人出场。他们对着镜头,用自己的记忆和印象,为观众拼凑起一个萧红。
要悉数将三十多人对号入座,即使对中国观众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鞍华解释,她执意要尝试一种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变成悬案,我们没有说给你们看一些什么定案的东西,只是根据一手资料,她自己写的、朋友写的,整理出来。有疑案,就告诉你是个疑案。”
从观众反应来看,这并不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实验。“许鞍华的野心很大,她想在这部电影里放进很多大格局,那个文人辈出的民国时代,还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政治性和个人选择的冲突,重新树立一种传记片的标准……但恰恰是这些野心束缚了她,造成了《黄金时代》的问题。”《综艺》杂志这样评论。
2011年,许鞍华在威尼斯电影节展映的影片《桃姐》,获得来自西方观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桃姐这位温柔的、有质感的,具有低调的人文精神的女性,也是许鞍华身上完美的电影标签。”
许鞍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履行“地平线”单元评委主席职责。有别于金狮奖,地平线单元重点鼓励电影的实验和创新,以捕捉世界电影未来的潮流和趋向。
“很多国家的名字我都不认得,但很多电影拍得非常好。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都是新的导演,他们去西方的电影学院学习,然后回他们国家自己拍戏。”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这些影片中,许鞍华看到如今世界艺术电影的三股“潮流”:一类是反映现代年轻人的虚无,“割手、吸毒、流浪不回家,然后特别理直气壮”;一类她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故事,比如阿拉伯地区战争的题材,或者在中东战火纷飞的背景下,一个老妇人独自生活的故事;还有一类,就是传统的批判题材,比如控诉某种制度。
最容易打动她的,首先是那些批判性的题材,“最后那个判断是什么不重要,呈现最重要,如果你能投入他所呈现的东西,你就受到教育了。”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在许鞍华看来,是一次学习世界电影怎么讲故事的过程。“学习人家的东西,不一定是技术,而是文化上的东西——他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太紧张、太害怕了,怕我们的片子不得奖,就没有时间去欣赏别人的电影。但这才是电影节最重要的。”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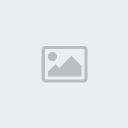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