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在叙利亚霍姆斯遇难的两名记者的遗体抵达巴黎机场。11天前,一枚炮弹击中叙利亚霍姆斯市一个“临时媒体中心”,美国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在袭击中身亡,另有3名记者受伤。
在炮火重重,宣布“对入境记者格杀勿论”的叙利亚,记者的处境变得越发危险。就在这两位记者遇难后的4天后,2月26日晚,一支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敢死队”试图将4名外国记者护送出国,但他们一路遭到政府军的阻击,最后只成功把英国记者康罗伊送到黎巴嫩,其他记者下落不明,“敢死队”队员13人被打死。记者的危险处境再次被推到了世界的焦点中。
关键词
国际主义者
对于在叙利亚的炮火中遇袭身亡的记者,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微博)用了“牺牲”这个词来形容。“牺牲与一般的被炮火打死不一样,他们是为了揭示真实而死,所以他们是崇高的。”唐师曾说。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是唐师曾认为真正的战地记者都应具备的素质。唐师曾说,真正的战地记者不属于某个立场或者某个集团,立场是真实,而不是评判分析,那不是记者应该干的事。
上大学的时候,唐师曾偶然接触到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传记,当时就“想当他这样的人”。在唐师曾眼里,卡帕是特别典型的国际主义者。卡帕有波西米亚血统,出生在匈牙利,在德国大学学政治,在法国照相谋生,在西班牙作战,在北非作战,在巴黎恋爱,后加入美国籍,在日本上班,在越南采访时死于炮火,最终埋在美国。
“从他一生的轨迹来讲,很难说他属于哪儿。他没把自己跟一个强大的集团或集体绑在一起。他始终追逐他的真实,围着世界绕了一圈。”唐师曾说:“在卡帕这条路上,在叙利亚牺牲的那两个记者跟我算同志。”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39岁的唐师曾只身“潜”往伊拉克,最后才撤离巴格达;辗转敌战双方,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以色列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之后三年,他成为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四处奔波,走访了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一大批世界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关键词
自由撰稿人
在海湾战争中,唐师曾的单枪匹马其实也是大多数战地记者的工作状态。单枪匹马的状态,并不只是指记者们总是孤身一人,而是他们很多是如同罗伯特卡帕一样,生命是漂浮的,并不属于哪一个单位。即使他们供职于美联社、路透社,也都是“临时工”。“在战地与别人在一起,也是保全自身的策略。”唐师曾说,在伊拉克的时候前往约旦河谷,就是与其他几个国家的记者同行。“如果你是一个人失踪了没有人会找你。但国籍多就不一样,人丢了会对好几个国家产生影响。”
“这一行最牛的记者都是free-lance(自由撰稿人)。”唐师曾说,很多有名的记者都是自由撰稿人,他们并不以经济或者政治利益为目的,而是忠于他们自己的心。当自由撰稿人是对战地记者最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单位对记者都有限制,而自由撰稿能把它降到最低甚至消除。”
唐师曾说,我在中东那一带认识的战地记者,有些都在阿拉伯安家了,这样他们更能得到一线新闻,当地人会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消息给他们。
关键词
创伤
即使没有在炮火中牺牲,战地记者们也不是那么幸运。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安东尼•费恩斯坦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战地记者比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受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3倍多。4个战地记者中至少有1个接受过战后心理诊断,比例比上过战场的老兵还高。
唐师曾也未能幸免。由于长年在战乱国家辗转奔波,唐师曾受到了辐射,不幸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和重度抑郁症。“现在不行了,综合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唐师曾感叹道,“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等待的时刻,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发生爆炸或者枪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跑是一种综合起来的茫然虚无。”
在战地,不仅要面对未知的恐惧,还要克服对战场的残酷。唐师曾第一次来到巴格达的时候,战火还未起,美丽富饶的伊拉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亲眼看到伊拉克毁于炮火,唐师曾的心情是复杂的。
即便这样,他到如今却仍“后悔当初没有胆子更大,走得更远。” 唐师曾说,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之轻》里有一句话:有的战争是有意义的,有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只不过是人类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平常也有。战争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勇敢、诚实的人会在战争中获胜。”
声音
战地记者手中的赌注就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
抬起一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有可能踩到地雷。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大代价?我们能不能带来变化?在我眼睛受伤的时候,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值得,我现在也会这么回答。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出真相。
——科尔文
作为摄影师,最痛苦的莫过于觉得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上。这令我每天挣扎不已,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让个人野心盖过真正的同情,我就出卖了灵魂。
——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赫特韦
两个葬礼与一场婚礼
2011年的7月11日,“85后”的凤凰卫视记者马骋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正处于战乱之中的利比亚,驻扎在班加西。
开始的时候,马骋还带着疏离感,随着与身边利比亚人交往的深入,与这片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都结识了一些利比亚的朋友,我们的翻译穆罕默德在斋月的时候会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还有酒店的女佣等,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
在听到了很多此前卡扎菲的暴虐行径以后,马骋与同事们对他们也心生无比同情,也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战争爆发后,很多人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非常窘迫。“所谓‘一战成名’的想法几乎没有,只想能称职地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从战地回来后,你会有种犯瘾的感觉想再回到那样的氛围中。”
在利比亚的一个多月,马骋经历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两个葬礼和一场婚礼。2011年7月29日,马骋参加了反对派军事总指挥尤尼斯的葬礼。“当时国内的同行都觉得危险没有去,我们的翻译当天做礼拜也不愿意开车来拉我们,找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拉我们到了墓地,一路上枪声不断。”他回忆。
在尤尼斯的灵柩下到墓地时,枪炮向天射击以示哀悼,飞散的子弹壳像雨滴一样洒落,“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地面在震颤,几乎站立不稳。”
2011年8月的一个下午,马骋和同事们又参加了一位利比亚反对派战士穆斯塔赫的葬礼。在布雷加前线作战的亲属们得知死讯,三三两两来到他的家里表示哀悼。更远一些的地方,枪声则断断续续;为死者诵读古兰经的平和安详与子弹刺耳的呼号就这样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为了理想,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呢?生命么?”在这样的时刻,马骋这样问自己。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一场婚礼。2011年7月17日傍晚,在利比亚班加西一个普通社区,一个红色中国灯笼高高挂起,一场战争中的婚礼正在举行。
30岁的新郎阿克曼穿着笔挺的西服,很难想象仅在一周前,他还在前线与卡扎菲的武装战斗。结婚自然是人生乐事,然而卡扎菲并未倒台,自己还不能真正享受新婚的喜悦。阿克曼对马骋说:“为了使利比亚在未来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我愿意做任何事。”婚礼后一周,他重返米苏拉塔前线。
这场婚礼带给了马骋深深的思考。“从那个晚上开始,发生在利比亚的战争,于自己不再是无关的看客,我们都是战士,不过战斗在不同的战场上;他们追寻的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我们追寻的,是自己的新闻理想。从那个晚上开始,子弹的呼啸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相关人物链接——唐师曾
唐师曾,毕业于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任新华社主任记者,装甲兵学院研究员,荣誉陆军上校,美国柯达联网职业摄影师。在完成新华社图片文字发稿任务之余,在《世界博览》等报刊发表文字数十万字。2001年5月4日,当选“全国十大新锐青年”。几年来,洪水、大火、地震、骚乱、瘟疫、战争......唐师曾多次冒生命危险亲临一线采访,为新华社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照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英才》、《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香港《影像中国》画报、《中国青年》、 德国《鲁尔日报》、《香港商报》、《约旦时报》、《埃及华夫脱报》、《以色列消息报》、路透社电讯、法新社电讯、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有线电视网、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卫视等近百家传媒多次报道过他的传奇。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
“它”值得我付出所有
2012-02-27 06:08:00 来源: 钱江晚报(杭州)
2012-02-27 06:08:00 来源: 钱江晚报(杭州)
2012年,2月22日,叙利亚霍姆斯继续战火纷飞。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玛丽•科尔文感觉到很无助。她在脸谱的个人主页上写道:“我感到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跟踪报道(叙利亚动乱)。” 她和自己的朋友在脸谱上聊天,希望他们能够为这个地方提供一点帮助。然后,她通过电话告诉BBC, 一名两岁男童死于炮弹碎片。
而数小时以后,火箭弹就从天而降,56岁的玛丽•科尔文被火箭弹击中身亡。同时中弹的还有另外一位年轻的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目击者阿布•巴克尔说:“房子遭到袭击之后我逃了出去,跑向街对面的房子。袭击还在继续,记者们的尸体就躺在地上…… ”
大学毕业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都是记者
科尔文1956年1月12日生于纽约长岛,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中学时因表现优秀,科尔文获得赴欧洲交流一年的机会。交流生活拓宽了科尔文的视野,在1974年高中毕业那年,她决定放弃社区大学的奖学金,转而向耶鲁大学挑战。最终,科尔文以优秀的表现获得面试老师的认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大学期间,科尔文加入了耶鲁校报,一度以为自己“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而已,但大四那年她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研讨会上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科尔文回忆说,“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
1978年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1986年,她加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逐渐成为资深的战地记者,在这家报社一直干到她去世那刻。
丢失了一只眼睛,也要向战地前进
2001年,科尔文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碎片击中失去一只眼睛,从此“独眼龙”眼罩成了她的标记。此后,她喜欢在失明的那只眼睛上戴个眼罩。
她的手上总是拿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每次她总是会第一个抵达事发现场,就在遇难前一天,她作为现场 “唯一一名英国媒体记者”,也是这么做的。她也因为自己的勇气和执着受到大家的爱戴。
科尔文是真正的战地记者。过去30年里,她报道过数场战争,包括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阿拉伯地区的动乱等,其间获奖无数。她去年曾亲历埃及和利比亚的变革,还采访过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这朵“铿锵玫瑰”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曾坦言,叙利亚是她经历过的最凶险一役。
她上周准备进入叙利亚时,她和朋友还多次交换意见,设计进入霍姆斯的路线,评估可能面临的风险。但要去见证和报道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所有恐惧,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
21日写完一篇稿子后,她在“脸谱”上告诉朋友,霍姆斯的情况有多糟。玛丽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都是需要付费阅读的,因此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于是她在“脸谱”的战地记者群里鼓励大家转发她在霍姆斯的报道。从技术上来说,她并不能这么做,因为她会因为导致报纸的收入流失而受到责难,但她觉得,霍姆斯的情况让她感到震撼和无助。
为了自己的使命付出最大代价
2010年11月,科尔文曾经在伦敦发表演讲,纪念在冲突中殉职的记者时说:“我们经常要自问,报道的内容值得你去冒多大的危险?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虚张声势的勇气? ”科尔文说,“报道战争的记者肩负重要的责任,也会面临艰难的选择。有时候,他们还会付出最大的代价。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职业,在冲突地带,记者就是主要的目标。 ”
“抬起一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有可能踩到地雷。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爆炸,这就是所谓的噩梦。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代价?我们能不能来带变化?在我眼睛受伤的时候,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那时候的回答是 ‘值得’,我现在也会这么回答。 ”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
【拓展链接】
http://topics.gmw.cn/node_24726.htm
战地记者,枪林弹雨中传递真相
http://mil.gmw.cn/2011-11/08/content_2930213.htm
记者节图刊——战地记者:我是个没有枪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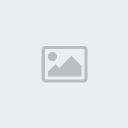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