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麻心汤圆
2014-01-22 10:20 作者:陈赛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01-22 10:20 作者:陈赛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对麻心汤圆的记忆,几乎就是关于童年最初的记忆。那些薄雾蒙蒙,呵气成霜的清晨,我们挤在外婆的小床上,裹着厚厚的被子,透过小窗,瞪着窗外光秃秃的树影,等着公鸡打鸣,天色泛白。
至今我仍很难想象当年外婆那张小床上,为什么能塞下四个活蹦乱跳的小孩。我们缩在被窝里,互相扯着被子,想把自己裹得再严实一点。正在纠缠间,从楼下传来一阵淡淡的、清澈的糯香,突然间谁都不怕冷了,争相从被窝中跳出来,光着脚丫就往楼下跑去。
四个人排排坐在小板凳上,每人面前一个小碗,热腾腾的冒着气,里面躺着七八个硕大的汤圆,雪白剔透,上面细细碎碎撒了一层金黄的桂花,香气扑鼻。
我们比着各自碗里汤圆的多少,个头的大小,一边向外婆抗议着莫须有的偏心,一边迫不及待地一勺下去。汤圆实在太大,一口吞不下,只觉得一团滑溜溜,软糯香甜的东西在嘴里化开,滚烫的芝麻缓缓流出,味蕾瞬间开出一朵朵花来。
我一向不喜欢甜食,唯有麻心汤圆例外。每年冬至,都要买上一包,但总没有童年时的滋味。大概是记忆和距离美化了当年的味觉吧。毕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吃过外婆做的麻心汤圆了。
在我们那个江南小镇,老人们也管冬至叫“冬节”,冬节要吃汤圆,尤其是小孩子,吃了汤圆,才算长了一虚岁。事实上,过年的气氛就是从冬至前后慢慢酝酿起来的。经历了“十月末,水冰骨”的寒流后,阴雨绵绵的天气逐渐放晴,变得干燥,适宜晾晒。不少人家会提前几天将糯米碾成粉,用水拌糊,然后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摆在竹笪上晒成汤圆粉。汤圆粉晒干后放入洋油箱,要吃时拿几块出来用水浸开后使用。除了麻心汤圆之外,汤圆还有很多种吃法,比如醪糟汤圆、桂花汤圆,或者做成咸的(实心小汤圆清汤煮后加入肉丝、笋丝、虾皮、紫菜等汤头),或者擂成麻糍(方块状的糯米团子经清汤煮后,在麻糍粉中搅拌)……
除了晒汤圆粉之外,家家户户的院子里还开始陆续挂出酱油鸡、酱油鸭、酱油肉,长长的竹席上晒满了各种鱼鲞,小黄鱼、白果子、鮸鱼、鳗鱼、乌贼干……一些心急的人家,甚至开始熬起了肉冻。一个大蹄髈,一只老母鸡,放入酱油、老酒、糖、盐,炖上七八个小时,直到肉和骨头都融成一锅浓汤,然后找家里最大的碗盛起来,放到窗外冻一夜。第二天一早,刮去上面一层白白的猪油,就露出晶莹剔透的肉冻。
我的童年,还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过年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制造一种哪怕是暂时的富足感——水缸里装满年糕,酒坛里盛满美酒,橱柜里有随时可以拿出来待客的菜肴,罐子里有源源不断的糖果、花生、瓜子……
按家乡的旧习,新年的第一天要扫墓祭祖,第二天是父亲家族的新年酒,到第三天才是母亲家族的拜年。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去外婆家拜年,是过年的最高潮。
外婆住在隔江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现在只要20分钟的车程,30年前却要几经跋涉,而且都是水路,先坐渡轮过江,改乘小船过河,再换人力车,再步行……对没出过什么远门的小孩子来说,那是一年一度隆重而意义非凡的旅行。我至今记得母亲给我买的一双绿色小皮鞋,那是我生平第一双皮鞋,迟迟不舍得穿,一直等到要去外婆家了,才郑重其事地拿出来。穿上带蕾丝的白色小棉袜,扣上小皮鞋的扣子,听着皮鞋敲击地面清脆的声音,我是怀着怎样骄傲而快乐的心情,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光。
父亲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螃蟹、血蛤、海蜇皮,母亲提着各种干货,对虾、乌贼干、鳗鲞……我负责拿轻一点的东西,炒米糖、芝麻糖,还有外婆最喜欢吃的炒豌豆。她牙口不好,却独独中意炒豌豆“喷喷香”的味道。我热衷于这个还因为,我和表妹最喜欢玩撒豌豆的游戏。一把豌豆撒下去,用一颗豌豆去碰撞另一颗豌豆,碰到的就可以收到自己的囊中,简直有点像打斯诺克。至于弟弟,他只负责拿自己的烟花爆竹。小火箭、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基本上他每年的压岁钱都花在了这些烟花上头,这也让他成了外婆家附近小男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城里人”。
记忆中,去外婆家的路上,就是一条河连着一条河,一座小桥连着一座小桥,岸边是一片片的水田,冷清清地留着粮食收割之后一丛丛的稻茬和草垛。老水牛懒洋洋地躺在田间淤泥里,硕大温顺的眼睛瞪着天空,一动不动。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鲜艳的风景,比如冬天里绿意正浓的菜籽薹。母亲常常会停下来,跟农家买几株,带到外婆家炒年糕吃。新年酒的头盘,常常就是从一道菜籽薹炒年糕开始的:雪白的年糕,紫红的酱油肉,金黄的虾米,碧绿的菜籽薹,顶上还带着刚开的小黄花。
就这样一路下来,从八九点出发,常常要到中午,才能到外婆家。表弟表妹早已守在村口,在田间地头游来荡去,东张西望,用外婆的话说,跟“猫等耗子似的”。他们是大舅舅的孩子,表弟叫永定,表妹叫和平,与我和弟弟差不多年纪,是我们童年时最亲密的玩伴。
“外婆,外婆……”还隔着老远的路,我们已经一边叫喊着一边朝外婆飞奔而去,把父母远远地落在后面。记忆里,外婆总是笑吟吟地立在门口,拂一拂灰白的头发,轻轻抱住我们问道:“来啦,饿不饿?”然后立刻下厨给我们做一碗醪糟鸡蛋,或者一碗素面汤,上面铺满切得细细的金黄的蛋丝。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对人的疼爱,永远是喂饱了再说。
外婆一共有五个孩子,母亲是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出于乡下一种奇怪的规矩,他们都不管外婆叫妈,而是叫“阿婶”。据母亲说,这是假装过继,为了孩子好养活。但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没娘的孩子好养活?
那时候,几个舅舅都还住在一起,一排五间的两层小楼,外婆和小舅舅住在最边上的一间。陈旧泛白的木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门檐上挂着“五好家庭”的牌子。
外婆的厨房很狭窄,却有一个大的不成比例的灶台。是烧柴火的那种老式灶台,两口大铁锅,够煮十来个人的饭菜。我很喜欢用那口锅做出来的白米饭,尤其是底下一层薄薄的锅巴,趁热可以完整地剥下来,暖暖的,软软的,卷一卷,蘸点白糖,就是最美味的零食。
记得我们几个小孩经常被差遣去附近的小树林找枯叶、稻梗和掉落的树枝,谁捡得多,压岁钱就会多几枚硬币。南方的冬天奇冷无比,灶炉边是整个屋子最暖和的地方,所以每次外婆煮饭,我们都争着去烧火,而且很快掌握了控制火候的办法:火大了,就加点湿木棍;火小了,加点小的干树枝和树叶,火自然就变得又凶又猛。
因为灶台太大了,整个厨房就只塞得下一个小橱柜和一张小圆桌。那是外公在世的时候亲手做的,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至今仍然摆在外婆的厨房里,摸上去就像新的一样,细闻之下还有樟木淡淡的香味。当时我们还太小,当然不懂得外婆在这些遗物中倾注的深情,但那个橱柜对我们而言多多少少有点像美丽的魔法,里面总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糖果和零食。而且,外婆的炒米糖特别脆,芝麻糖特别香,芙蓉糖特别甜蜜粘牙……
厨房里没有自来水,洗菜要到院子里去,几个舅舅合力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井水又深又冷,冬天把手伸进去能冻到神经麻痹。但外婆用它来洗菜刷盘,虎虎生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外婆信佛,常年吃素,唯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她镇定地杀鸡宰羊,仿佛这番杀生,是经过了佛主的默许——刚炖好的老母鸡从脸盆里直挺挺地伸出两条肥嫩的腿,还在水里满口吐泡沫的大螃蟹、游来游去滑不溜秋的河鳗、金灿灿的小黄鱼张着嘴巴、墨黑的乌贼,洗得雪白的血蛤……我喜欢看她和母亲在灶间忙忙碌碌的身影。洗洗刷刷,烧炒煎炸,大勺小勺、油盐酱醋递来递去,仿佛操持一场千年不散的宴席。
比起酒席上正襟危坐的大人们吃的大鱼大肉,作为小孩子,我们更喜欢私底下跑来跑去要吃的。闻到蒸锅里腊鸡的香味出来了,就巴巴地跑来讨一根腊鸡腿吃;螃蟹煮熟了,四个人先上来瓜分掉四颗大螯;血蛤烫好了,赶紧趁热拨开几个尝鲜,吃得一口血淋淋的;荸荠削好了皮,雪白可爱地摆成螺旋状的一盘,我们就从底座偷几颗揣兜兜里,一会儿玩累了解渴。那时候还没有草莓、樱桃之类的舶来水果,荸荠就算是最美味爽口的水果了。跟着我们穿梭往来的,还有一只瘸了腿的狗。它本是山上一只野狗,被一群恶作剧的小混混用鞭炮炸掉了尾巴和一条后腿。外婆可怜它,每次都给它留一些剩菜剩饭,它就从此寸步不离地跟在外婆身边。遇到这种盛宴,它自然也要来讨几根肉骨头吃。
有时候,我们会乖乖地坐下来,给大人帮帮手,比如帮外婆包麻心汤圆。外婆早已把面团揉好,揪成一小块一小块,给我们每人分几块,在手心摊成薄薄的圆形,在中间放上一颗黑芝麻球(由芝麻、白糖、猪油搅拌而成),小心地收口,再在手掌间轻轻揉搓,把一个个汤圆搓得又大又圆。外婆总是在一旁笑眯眯地说,一定要搓的圆圆的啊,那样才能团圆呢。
如果汤圆粉有盈余,再加上我们的软磨硬泡,外婆会用剩下的一点汤圆粉给我们做油泡丸吃,那是我们童年时代的最爱。油泡丸,其实就是油炸糯米丸子。糯米粉里加些白糖,随手捏成一个个圆形的小丸子,在热油里炸开,直到炸得通体金黄酥脆,才捞上来。常常是外婆刚捞上来一个,早已被我们迫不及待地抢着塞嘴里了,一边吃一边咂嘴巴,满嘴油光,心满意足。
汤圆粉是三舅舅送过来的。四兄弟中,三舅舅是唯一一个一直靠种地为生的人。他为人最为憨厚老实,又娶了一个很厉害的舅妈,平常走路说话总有点讷讷的感觉,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暗地里可怜他。但每年腊月,他都会千里迢迢地给我家送来年糕、糯米粉和米酒,尤其是一种叫“蜜蜜橙”的黄酒,爸爸至今念念不忘。那是一种很特别的黄酒,橘黄色,看上去有点像蜂蜜,只是更清更亮。就装在毫不起眼的塑料水桶里,但一打开,满屋都是异香。那是三舅舅亲自酿的——每年他都会留下两块地专门种糯米,一块用来做捣年糕,磨糯米粉,另一块用来酿酒,“蜜蜜橙”大概就是最精华的黄酒。当他在酒席间拿出“蜜蜜橙”给众人斟酒时,在啧啧的赞叹声中,那略显愁苦的脸会一下子舒展开来,简直是神采飞扬起来。
我和表妹喜欢躲在外婆的阁楼里玩。阁楼是外婆睡觉的地方,地板很老旧了,踩上去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那是一个再简陋不过的房间,只有一张小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面镜子、一个梳子和一张外公的遗像。那是外公留在世间的唯一一张照片:穿着旧T恤,背一个黑色的挎包,才40岁,头发已经花白,但笑得很爽朗的样子。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能用笛子吹很好听的曲子。外公是我出生那一年去世的,“文革”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早晨,他的尸体被发现漂流在附近的小河。关于他的死,至今是一个谜。
表妹两岁的时候从楼上摔下来,大病一场。外婆梦见外公说,“小孙女真可爱”。外婆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让他离表妹远一点。第二天,表妹的病就好了。这些都是在那个小阁楼里,表妹当成家族秘史说给我听的。她说,在这个家族里,作为外孙女,毕竟是个外人,所以很多事情并不知道。
外公就葬在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都是一座孤坟,黄土草草垒就,四周荒烟蔓草,满目凄凉。但坟前有一株杨梅树,每年清明时节,杨梅熟时,当真一个个紫盘绿蒂,甜美无比。所以,给外公上坟,对我们来说绝无阴森之感,而是一场美妙的冒险,我们能爬到那棵杨梅树上吃上整整一个下午,直吃到舌头变紫,牙根发软。通常是小舅舅带着我们,他就比我大5岁,是我们中间的孩子王。他教给我们乡间小孩的各种游戏,挖野菜、捉蛐蛐儿、掏鸟蛋、摸螺丝、抓鱼、游泳……最近一次见到他,他已经四十出头,生意失败,欠下一笔巨额债务,饭桌上只顾闷头喝啤酒。我总想起当年那个清俊的少年,每年夏天坐着小船给我们送来一捆新鲜的甘蔗。
给外婆拜年,照例也要给外公上坟扫墓。舅舅们带上柴刀、鞭炮和爆竹,先用柴刀将外公坟墓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放鞭炮和爆竹,这是告诉外公,子孙们来看望他了。
外婆并不跟我们一起上坟。当酒席终了,客人散去,一切收拾完毕,她终于可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晒会儿太阳,喝碗浓茶,听会儿弹词。弹词是南方的一种戏曲,用我们当地的方言唱的,外婆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唱的无非是些才子佳人、负心薄幸的故事,伴着寥落的几声琵琶与三弦,听着多少让人心生悲凉之感。多年以后,母亲身患重病,癌细胞侵入身体各个器官,唯一能让她快乐起来的事情,就是让我陪着去外婆家,也是这样躺在院子里,冬日的阳光正好,与外婆一起晒晒太阳,听听弹词。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可以静止,拯救我们不向命运的深渊继续滑下去。
小时候在外婆家,总嫌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向父母各种撒娇耍赖,希望能在外婆家里多留宿几晚。我们愉快地伴着外婆的鼾声入眠,期待着第二天一早,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麻心汤圆。但如今,表弟远在俄罗斯做生意,表妹嫁到上海,我在北京定居,只有弟弟还留在老家。几个舅舅陆续搬离老宅,只剩下外婆一个人还住在那个小屋里。更没想到的,是母亲过早地离世。外婆在经历了人世最不幸的伤痛之后,变得更加的消瘦与沉默。我想,就算她再做一碗麻心汤圆,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滋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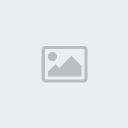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