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正文】
王维生活的唐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所谓“高宗天后,访道山林”使得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家的返朴归真,佛家的静心明性,为文人的漫游隐居,情性空灵提供了心灵上的关照。因此,犹如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相互交融的内核一样,文人内心一直处在出世入世之间,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栖幽隐逸,湛然常寂,而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徜徉。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儒家用时济世的思想,锐意进取,所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在《献始兴公》诗中,盛赞张九龄写道:“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向张九龄求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些可以窥知王维早年的出仕态度,也可以窥知王维诗文才艺系着他的仕途。
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人,父处廉,官终于汾州司马,后移居蒲州,因此,王维籍贯为蒲州河东,因居京师,又称京兆人。王维多才多艺,诗、书、画、乐所无不通,《新唐书》写道“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十五岁时,有诗句“自有山泉人,非因彩画来”已见胸中丘壑。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在此之前,与他仕途有着密切关系的是他与贵族的交往以及他的诗文才艺。据《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岐王李范是睿宗的第四子,是玄宗的遗母兄弟,《旧唐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雅爱文士,不论他们贵贱贫富,一律以礼接待。由于岐王这种雅爱文士的个性,使他的宅第成为当时宾客云集的交往场所,而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同时岐王也擅长书法,对搜集书画古籍有着莫大的兴趣,这使得王维受到特别的重视,后来王维能以榜首通过京兆府试,据说岐王居间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岐王曾带着身穿锦绣华服,手抱琵琶的王维到公主府上奉宴,欲得公主的赏识,当时,王维仅为皙白的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而他弹抚的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更有数卷诗篇,令人惊奇不已,同时,王维****蕴籍,说话风趣淡雅,也为满座所钦重。当公主听到美妙的《郁轮袍》后,得知自己喜爱的一些诗篇是王维的作品时甚感惊奇,而王维也因此受到推荐,一举登第。当然,《集异记》所载的故事未必属实,不过,王维少年时才华出众确是事实。
王维的才艺虽然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也系着他的豪情和苦闷,王维的仕途没有太多的坎坷,却有许多的失意。任太乐丞后,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悲欢聚散之快,笑泣转化之急,是王维无法预料的。此时,在几年的半官半隐,漫游山水,情性空灵中,王维渐渐地有了退隐的思想,而诗文中也有了前途难测的隐忧。王维返回长安之后,结识了山水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襄阳人,少尚节义,曾隐居鹿门山,开元十六年,孟浩然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王维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为他郁郁不得志,心中苦闷一时所发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时常闲赋,心中不是滋味。
然而,王维尽管修佛养道,情怀旷宇,劝孟浩然归庐隐居,但是自己却无法忘怀仕途,时常有求时济世之志,王维曾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与东都洛阳相近,隐于此地正可以待机而出。次年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后迁殿中传御史。就这样在闲居和官职变换中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进而中年,或隐或官,总不得意。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使,李林甫任中书令。李林甫排斥异己,又宠用蕃将,这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王维在《记荆州张丞相》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所谓“方将与农圃,艺植老秋园。”时感沮丧。但是他旋即奉使出塞,以监察御使衔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一直到了凉州。崔希逸击破吐蕃,意在保卫河西走廊。王维此行却写了不少意境宏阔、气势雄浑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气势豪迈,《使至塞上》自“单车欲问边”起,就笔力爽健,构景雄浑,结句“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绝奇豪迈,雄浑壮阔,有不尽之味,充分表现出盛唐气象。
王维的边塞诗可以体现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热情,开朗,雄心勃勃,创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光芒,饱含情韵。其中《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以急促的节奏,紧张的局势,关山飞雪,狼烟不举,强有力的氛围给人以振奋。而王维晚年却大相径庭,向往的“出世”,诗人久经仕途的失意,在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或者在佛家禅道影响下,悟到人生还有另一种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在半官半隐中更多了些“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思想。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往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由于他的诗名,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期间,安禄山曾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诗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由此可见他的心声依旧追随唐王朝。
然而,在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之后,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按律当斩。有人以王维的《凝碧池》诗见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赐免,并且任王维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尚书右丞,这是王维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惨痛遭遇的王维,晚年苦行斋心,“不衣文采”,除了饭僧施粥之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山庄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王维也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的《谢除太子中允表》和《责躬荐弟表》,可以窥见安史之乱时被拘于贼中的王维,曾一度想出家修道。
从“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道家自在无为的思想,这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中有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于是,诗人独坐,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着青苔色。无论如何添了一份“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闲趣。而在闲趣之中,物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这正是道家艺术的完美体现。
此外,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也有这般风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道家自然的意念,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恬静安宁的心境,与他追求清幽绝俗,自然坐忘的意趣相融合。《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将伤感的激愤和清冷的孤独的心境化为虚静至极、自在见性的境地。而《辋川集》中的《鹿柴》,“返景入深林”,在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里,有一种“忘我忘情”自得之乐,少了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
与佛家定慧参禅,静坐忘己的虚寂境界不同的是,道家没有来世之说,人生是苦海,断绝烦恼,因果报应只是佛家修禅达到的寂灭境地所需的历程。而道家坐忘修身,静坐忘己在于修身远祸,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以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待自由。而这一思想在王维的生活中也有反映。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在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王维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无能为力,他欲求摆脱这种痛苦,又时常摆脱不得,因此,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在辋川期间,他时常与裴迪赋诗赏玩,在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宫槐陌、临湖亭等地都留有他的绝句,以寄托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
而这二十首咏辋川的山水五绝《辋川集》,以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高落寞的情怀,蕴涵着清淡自然的道家风味,创作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其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明代胡应麟曾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辛夷花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正如诗人面对自然地零落,刹那间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
王维的逝世也如辛夷花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记载,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历代知识分子,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者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而王维也是如此,作为继六朝大小谢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之后的唐朝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仕途上有着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在心灵上有着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然而,仕途的云诘波诡,险象环生,使他渐渐地明白,与他性情相融洽的不是忧心重重的仕途,而是心灵依傍的山水和淡然。
因此,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辛酸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踏入了人生“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境地之中,而这种道家思想的衍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绘画之中。
王维的绘画,奇妙入神,山、水、云、石被画家认为“天机所到”,世上难得一见。王维好画雪景,也常有剑阁、栈道、捕鱼、山居的描绘,沉静的田园意趣,远离尘世的风景,有着清新脱俗之感,将渔人村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山居野趣,也点缀在悠闲清雅的画面之中。“富贵山林,两得其趣”,既是历代名士的向往,也是半官半隐,漫游山水之间的诗人的向往。王维还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芭蕉”的意喻得到后世的推崇,这种超越于常理之外的艺术创作,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深化了“得意忘笔”的玄理思想。
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毕竟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变化。而王维在仕途受挫,感怀现实之中,得以栖幽隐逸,湛然常寂,得以超越世事、解脱困惑,以达自然自在和自为。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原文地址: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28/2049604.shtml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28/2049609.shtml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正文】
王维生活的唐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所谓“高宗天后,访道山林”使得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家的返朴归真,佛家的静心明性,为文人的漫游隐居,情性空灵提供了心灵上的关照。因此,犹如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相互交融的内核一样,文人内心一直处在出世入世之间,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栖幽隐逸,湛然常寂,而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徜徉。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儒家用时济世的思想,锐意进取,所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在《献始兴公》诗中,盛赞张九龄写道:“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向张九龄求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些可以窥知王维早年的出仕态度,也可以窥知王维诗文才艺系着他的仕途。
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人,父处廉,官终于汾州司马,后移居蒲州,因此,王维籍贯为蒲州河东,因居京师,又称京兆人。王维多才多艺,诗、书、画、乐所无不通,《新唐书》写道“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十五岁时,有诗句“自有山泉人,非因彩画来”已见胸中丘壑。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在此之前,与他仕途有着密切关系的是他与贵族的交往以及他的诗文才艺。据《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岐王李范是睿宗的第四子,是玄宗的遗母兄弟,《旧唐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雅爱文士,不论他们贵贱贫富,一律以礼接待。由于岐王这种雅爱文士的个性,使他的宅第成为当时宾客云集的交往场所,而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同时岐王也擅长书法,对搜集书画古籍有着莫大的兴趣,这使得王维受到特别的重视,后来王维能以榜首通过京兆府试,据说岐王居间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岐王曾带着身穿锦绣华服,手抱琵琶的王维到公主府上奉宴,欲得公主的赏识,当时,王维仅为皙白的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而他弹抚的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更有数卷诗篇,令人惊奇不已,同时,王维****蕴籍,说话风趣淡雅,也为满座所钦重。当公主听到美妙的《郁轮袍》后,得知自己喜爱的一些诗篇是王维的作品时甚感惊奇,而王维也因此受到推荐,一举登第。当然,《集异记》所载的故事未必属实,不过,王维少年时才华出众确是事实。
王维的才艺虽然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也系着他的豪情和苦闷,王维的仕途没有太多的坎坷,却有许多的失意。任太乐丞后,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悲欢聚散之快,笑泣转化之急,是王维无法预料的。此时,在几年的半官半隐,漫游山水,情性空灵中,王维渐渐地有了退隐的思想,而诗文中也有了前途难测的隐忧。王维返回长安之后,结识了山水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襄阳人,少尚节义,曾隐居鹿门山,开元十六年,孟浩然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王维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为他郁郁不得志,心中苦闷一时所发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时常闲赋,心中不是滋味。
然而,王维尽管修佛养道,情怀旷宇,劝孟浩然归庐隐居,但是自己却无法忘怀仕途,时常有求时济世之志,王维曾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与东都洛阳相近,隐于此地正可以待机而出。次年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后迁殿中传御史。就这样在闲居和官职变换中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进而中年,或隐或官,总不得意。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使,李林甫任中书令。李林甫排斥异己,又宠用蕃将,这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王维在《记荆州张丞相》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所谓“方将与农圃,艺植老秋园。”时感沮丧。但是他旋即奉使出塞,以监察御使衔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一直到了凉州。崔希逸击破吐蕃,意在保卫河西走廊。王维此行却写了不少意境宏阔、气势雄浑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气势豪迈,《使至塞上》自“单车欲问边”起,就笔力爽健,构景雄浑,结句“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绝奇豪迈,雄浑壮阔,有不尽之味,充分表现出盛唐气象。
王维的边塞诗可以体现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热情,开朗,雄心勃勃,创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光芒,饱含情韵。其中《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以急促的节奏,紧张的局势,关山飞雪,狼烟不举,强有力的氛围给人以振奋。而王维晚年却大相径庭,向往的“出世”,诗人久经仕途的失意,在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或者在佛家禅道影响下,悟到人生还有另一种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在半官半隐中更多了些“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思想。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往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由于他的诗名,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期间,安禄山曾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诗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由此可见他的心声依旧追随唐王朝。
然而,在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之后,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按律当斩。有人以王维的《凝碧池》诗见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赐免,并且任王维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尚书右丞,这是王维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惨痛遭遇的王维,晚年苦行斋心,“不衣文采”,除了饭僧施粥之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山庄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王维也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的《谢除太子中允表》和《责躬荐弟表》,可以窥见安史之乱时被拘于贼中的王维,曾一度想出家修道。
从“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道家自在无为的思想,这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中有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于是,诗人独坐,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着青苔色。无论如何添了一份“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闲趣。而在闲趣之中,物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这正是道家艺术的完美体现。
此外,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也有这般风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道家自然的意念,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恬静安宁的心境,与他追求清幽绝俗,自然坐忘的意趣相融合。《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将伤感的激愤和清冷的孤独的心境化为虚静至极、自在见性的境地。而《辋川集》中的《鹿柴》,“返景入深林”,在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里,有一种“忘我忘情”自得之乐,少了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
与佛家定慧参禅,静坐忘己的虚寂境界不同的是,道家没有来世之说,人生是苦海,断绝烦恼,因果报应只是佛家修禅达到的寂灭境地所需的历程。而道家坐忘修身,静坐忘己在于修身远祸,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以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待自由。而这一思想在王维的生活中也有反映。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在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王维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无能为力,他欲求摆脱这种痛苦,又时常摆脱不得,因此,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在辋川期间,他时常与裴迪赋诗赏玩,在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宫槐陌、临湖亭等地都留有他的绝句,以寄托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
而这二十首咏辋川的山水五绝《辋川集》,以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高落寞的情怀,蕴涵着清淡自然的道家风味,创作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其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明代胡应麟曾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辛夷花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正如诗人面对自然地零落,刹那间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
王维的逝世也如辛夷花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记载,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历代知识分子,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者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而王维也是如此,作为继六朝大小谢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之后的唐朝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仕途上有着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在心灵上有着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然而,仕途的云诘波诡,险象环生,使他渐渐地明白,与他性情相融洽的不是忧心重重的仕途,而是心灵依傍的山水和淡然。
因此,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辛酸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踏入了人生“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境地之中,而这种道家思想的衍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绘画之中。
王维的绘画,奇妙入神,山、水、云、石被画家认为“天机所到”,世上难得一见。王维好画雪景,也常有剑阁、栈道、捕鱼、山居的描绘,沉静的田园意趣,远离尘世的风景,有着清新脱俗之感,将渔人村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山居野趣,也点缀在悠闲清雅的画面之中。“富贵山林,两得其趣”,既是历代名士的向往,也是半官半隐,漫游山水之间的诗人的向往。王维还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芭蕉”的意喻得到后世的推崇,这种超越于常理之外的艺术创作,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深化了“得意忘笔”的玄理思想。
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毕竟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变化。而王维在仕途受挫,感怀现实之中,得以栖幽隐逸,湛然常寂,得以超越世事、解脱困惑,以达自然自在和自为。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原文地址: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28/2049604.shtml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3-28/2049609.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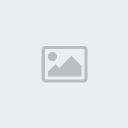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