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魂儿
<<新周刊>>第386期
<<新周刊>>第386期
做真心想做的事,听从内心而生活,这些人找到了他们的魂儿。
为留住记忆拍《一九四二》的冯小刚、在舞台上塑造孔雀之灵的杨丽萍、义务教拳倾囊相授的李学义、打理“爱心衣橱”以“干净”为生命的王凯、坚持音乐理想而甘之若饴的邵夷贝、寻找家乡味并记录寻常人命运的瞿筱葳、通过旅行认识自我的谷岳,这个世界的物质和欲望都如此丰盛,他们却不贪不急,选择做淡定的“一心人”。
温故的人 冯小刚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爱伦堡一个世纪前的这句话,在今天,像是说给电影《一九四二》的。冯小刚19年前读到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之后,就没再轻松过。冯小刚被历史的真实刺中,他决意要用电影去苦难中温故,带来千万人的知新。他拍了《一九四二》,把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到那段被遗忘的灾难,他迎接着非同寻常的尊敬和褒奖,也承受着预料之中的非议和冷漠。
“19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想,趁还有热情和决心的时候,要把《一九四二》拍出来。我也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条路很不平坦,很坎坷。这么多年拍成,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要知道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我觉得它值,它的意义超出了电影本身。”
从来得意于票房的冯小刚,面对这次情结之作,开始坦白因果:“我非常幸运,为了拍这部电影,之前也拍了很多赏心悦目的让观众开心的电影,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最后把他们骗进《一九四二》的电影院。”
有人不愿面对苦难。他们惦记着冯小刚的“喜剧之王”时代,面对沉重,他们吝于买单,甚至用娱乐的傲慢,怠慢了历史本身。冯小刚只能一声叹息。在2012的今天,他羡慕拍《辛德勒名单》的斯皮尔伯格。“犹太人不惧怕苦难,不回避,不会说生活太苦了,去找一个娱乐找补。他们一定会凝聚在苦难上,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他们生怕你忘了苦难。”
在终于得到刘震云的授权,两人商议《一九四二》剧本时,刘震云说了一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聪明人,一种人,是笨人。冯小刚接过话:《一九四二》这苦孩子面前,咱俩都是笨人。基调一定,两人选了最笨的方式:沿着小说《温故1942》中涉及的省份,一个村一个镇地走,沿路采访。
以前冯小刚电影的乐来得直接又理所应当,包袱包着机巧,眼睛盯着大众,轻而易举地挠着他们的痒穴,指挥着一整年的笑声。如今的冯小刚终于够本走回自己,走回一个电影导演的内心,走向一个意义本身。他在可以继续聪明的时代,选择了做一种笨人,笨得毫不犹豫。 (图—张海儿/新周刊 采访/ 张丁歌)
内观的舞者 杨丽萍
杨丽萍从小就在云南的庄稼地里面长大,在祖辈们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祭祀活动里学习舞蹈歌唱,很早就得到天地之气,由此开悟。这些自然的东西是成长在北上广这些城市的水泥墙里面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这是她身上最特别的东西。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永远挖不完的宝藏。在《雀之灵》之后,杨丽萍依旧是更多地向内观。她平静内心,把自己内心的小宇宙与外面的大宇宙连在一起,源源不断地采到很多气,得到很多灵感。如果她只是去模仿别人,自己的气场就断掉了。观众也只会说这里面是谁谁谁的影子,跟杨丽萍没关系。杨丽萍恰恰没有这么做,她是用自己的方式深挖自己的内心,内观是她的法宝。
杨丽萍在工作的时候非常执着,她的标准是一个最高标准。她不允许她的队员在舞台上有任何懒惰,哪怕是一小段她也会非常挑剔,常有队员受不了哭鼻子。今年我在昆明野生动物园拍摄她和孔雀在一起的照片。刚开始孔雀们也是和她对视,奇怪为什么外表很“孔雀”的杨丽萍会来到这里。后来孔雀们慢慢习惯了,她也就抱着孔雀让我帮她拍照。当时她躺在一个石头堆的斜坡上,那些石头堆非常硌,我没让她起来,她也就一直没动。她真的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敬业的人。我和她一样,都是在自己的行业里有很强烈的创作的欲望,所以才能够二十年来一直合作下来。
今年,杨丽萍又为观众带来了新作品——大型舞剧《孔雀》,讲述的是生命轮回:孔雀最初从一个雏形的蛋破壳而出,长大后经历了公孔雀和乌鸦的争斗,最后在神明的保佑下、在一片洁白的雪花中,领悟到了生命最宝贵的东西,灵魂飞上了天。如果说20多年前的《雀之灵》里面更多的是一些很美很炫的东西,如今杨丽萍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经历和经验不断累积,已经在舞蹈里探寻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了。她制作这么一场大型的舞剧,展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她惊艳的美貌和灵巧的身体,而是她积淀的智慧和思想了。(图、口述/肖全 采访整理/郑悦宇)
武术隐侠 李学义
小时,父亲常带李学义到南开花园玩耍。每当经过武术社看到里面有人练武,李学义就心生羡慕。“那时我才七八岁,家里条件很困难,也不可能一个月花两三块钱让我去学武术,那钱需要用来吃饭。”上初中后,父亲带他到单位一位武术老师处学八极拳。从此,李学义一生拳不离手。从师傅处学完拳回家,有时已经十一点多。李学义把自行车放下,在门口还要练一下,“把今天教的招式熟悉了,才进家睡觉。躺在炕上睡觉还睡不着,心里还在想招式是怎么走的。有些时候招式太复杂了,光躺在床上比划不出来,一着急干脆下地练。穿着裤衩背心,把招式都比划下来了,才回炕上睡”。
“文革”期间,八极拳老师因地主身份被遣送回乡,李学义转投八卦掌门下。1982年,师傅带着李学义到南开武术馆教八卦掌。那时的李学义武初有成,年轻气盛。一次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学员,以前练过少林功夫。李学义说:“好,那你用用。”学员一出手,李学义下手一摞,上手一个探掌打在他脑门上,差点栽了一个跟头。那人再也没有来学拳。多年以后,李学义明白了武术的真谛,深深责备自己,“练武也是练性子,不是让你越练越狂,到处跟人说你有武功”。
2002年,日本板神太极拳爱好会邀请李学义师兄弟三人到日本教学。“会长辻田先生没想到那次招生会来这么多人,整个大体育馆都挤满了,还要分成几个小组。 辻田激动得哭了。”李学义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也很感动。
如果不是这次出国要到单位盖章,同事还不知道单位里有一个武林高手。“同事都知道我会练,但都没看我练过,也不知道我练的什么东西。”李学义说。
李学义退休多年,还坚持每天一早骑车到南开大学校园内教拳。有时五点多就到,在树林里练完了,学生们才一个个地来。来一个教一个,“我教拳是无偿的,而且倾囊相授,我不会守着什么秘密不教徒弟”。李学义在练武与教拳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我教了很多学生,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我传授的技艺他们接受了,学习了,练习了,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图/王旭华 采访/邝新华)
做公益的人 王凯
2011年7月22日之前,王凯的名字让人联想起的关键词是“光头”、“早间读报”、“财富故事会”;7月22日之后,他的名字关联的关键词是“公益”、“爱心衣橱”、“央视主播慈善家”。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领头注册的“爱心衣橱基金会”,解决了5万多个孩子的穿衣问题,为山区贫困家庭送去了21万件衣物。
去年5月,王凯因一条转让二手衣物的微博,“歪打误撞”走上公益之路。那时,郭美美事件刚刚爆出,慈善成为烫手山芋。放下央视的话筒,王凯业余时间成为公益的主角,也成为争议的靶心。王凯放下狠话:我做公益正是时候,我要做一个最透明、走得最远的的公益机构。据说,爱心衣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启动的第一只公募慈善基金。“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必须明白,干净是它的生命。”
2011年 11月24日,第二届爱心衣橱慈善晚会在北京举行。没有时尚名媛、没有鸡尾酒会,只有一个比“财富故事会”时瘦了一圈的王凯,站在台上,面对几十家企业和数百位参与捐助的主持人、艺术家、演员等同道,一页一页“高唱账本”。他公布了爱心衣橱成立537天以来所募集到的所有善款数额和每一笔钱的去处。当晚拍卖,五个半小时,再次筹得善款近1100万。
如今的爱心衣橱基金会,专职人员不超过5个,却运转着越来越庞大的善款募集,和越来越精细的透明化账目机制。王凯这个主席,没有分文收入,却在央视两档节目之外,把业余时间的四分之三都扑在爱心衣橱上。“我们反而是赚到的人。赚到的是快乐,是受助人给了我们机会。”
王凯确信一个意识,做好事的机会特别值得珍惜。“公益是好事。为什么做好事?因为我们都想做一个好人。而好人是需要证明的,你不做好事,怎么证明做好人呢?每个人可能都有善念,但你真正去做了,落实了,才是善举。” (图—张海儿/新周刊 采访/ 张丁歌)
坚持音乐理想的文艺青年 邵夷贝
我从高中就喜欢摇滚乐,也就是大伙都喜欢的涅槃、电台司令那一批。那时候听这些歌,觉得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状态,愤怒而自我,想去模仿。几个喜欢摇滚乐的朋友还在一起做了本地下刊物,被学校大广播点名批评。也因为喜欢摇滚乐影响了高考,复读了一年,那一年窝在山里复习,一个月只放半天假,挺苦的。带了几张碟,有时候去小山坡上听一会儿。同学们都上大学了,给我写信说他们在北京看迷笛音乐节,看演出,那时候我就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北京。
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大二开始学鼓、组乐队、帮人写歌词。上研究生时也组了个女子乐队,我一直是鼓手。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已经在帮人写歌词,有点想走音乐这条路,但也不是全职。设想着一边工作,一边做自己的小Demo上传。
刚毕业后的那份工作,从单位到家就要三四个小时,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了。这份工作刺激了我,这种生活如果要持续到老,太可怕。所以我坚持写歌,去学了吉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后我都是一个打工的人,不再有冲动写东西,但至少我现在可以创作。相比起来,跟周围协调但坚持理想的苦,跟做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事的苦,好多了。
就算《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没有在网上红起来,我也依然会做音乐。这只不过是让我辞了职,做全职音乐人。那已经是我在网上上传的第三首歌了,是我音乐计划中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个音乐人,也有危机感,饥一顿饱一顿的。可能物质上没有多么好,但心里高兴,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我喜欢的事情上。我身边也有很多独立音乐人,没有一个因为工作放弃音乐,有些人已经坚持了十几年。这说明理想主义带来的愉悦,依然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图/王旭华 口述/邵夷贝 采访整理/于青)
留味行者 瞿筱葳
1939年,瞿筱葳的奶奶徐留云是个21岁的上海姑娘,未婚夫加入***撤退到重庆,她与另一个女孩渡船搭车,到四川找未婚夫。之后不久又因为战争一路逃亡,1949年随丈夫到了台湾。“我只知道她要从上海往西去四川,完全没有想其他,后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把我整理出来的五万字文稿画了路线图,我这才明白线路完全搞反了。”回过神,她决定用双脚重新经历奶奶当年走过的每一个城市,重新尝一遍家乡菜。2008年她以考察奶奶的食谱故事为题,申请到云门“流浪者计划”的奖助。
2009年6月,瞿筱葳在出发前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得很短。十公斤的背包里装着地图、五万字的口述史,还有一份奶奶原声录音。过去瞿筱葳的工作是将脚本化为影像,现在却必须将影像剪辑成文字。瞿筱葳说:“我的想法很单纯,想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去过哪些地方,她的菜是在哪些地方学会的。”伴着的汗臭、灰尘、油污一路前行。她把想法都记录在本子上,为防止加重负担,她尽量把字写得很小。为了更了解奶奶逃亡时的情景,她跑到图书馆查资料,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在到达宜宾时,她哭了,因为奶奶口述史中提到的地方都不复存在。在时空面前,她觉得自己孤独无助。
经越南、云南、贵州、四川,然后沿江而下,到达武汉、南京……旅行七十几天后,瞿筱葳终于在杭州的家常小馆,找到贴近奶奶手艺的菜肴。“过去我只知道我奶奶的菜混了很多种风味,后来才知道她一直是做家乡江浙一带的菜。”
流浪结束回到台北,瞿筱葳在奶奶去世后的房里剪接记忆,边写边哭。2011年11月,《留味行》出版了。瞿筱葳说:“小人物的小故事不应该只有被遗忘的命运。” (图/由被访者提供 采访/汪璐)
搭车去柏林的旅人 谷岳
2003年我辞职去旅行的时候没什么迟疑,觉得不想做这行了,虽然这份工作的报酬和前景都蛮好,但我没有收获感。本来是想在换一个行业之前,用半年的时间出去体验一下,没想到就成了两年。走了八九个月之后钱花完了,就在夏威夷打工,在餐馆里收盘子擦桌子,停车场收费、酒店里当礼宾。打完了工就去冲浪,想走就走。
回到北京之后,教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跟了一段时间的剧组,也有那么三四年,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对生活方向很忧虑。也考虑过做PR、市场之类的工作,但还是没做。后来成为自由职业者,做一些影视相关的工作,给外国的一些摄制组做东西。一般工作上几个星期或一个月,就等到把钱花完再说。而不管尝试什么,旅行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断过。
对我来说,旅行一方面是逃离现有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真正地去生活。在路上的每一天每一个目的地都是你自己的体验,而不是为了谁去做某件事。出发时我并没有想去通过旅行认识自己,但旅行完成后有这种感觉。在路上,有时你会无意识地被一个场景完全迷住,同时你突然又意识到自己时,就会有一种“了解”的感觉。十几年在路上是一种成长,最起码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在旅途中我觉得,人生中的体验是更重要的,物质反而是比较空虚的。
去柏林也好,去南美也好,我在乎的是经过。当你走出熟悉、安全、了解的环境内,在完全一个新的环境里时,才会感觉到“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图/由被访者提供 口述/谷岳 采访整理/于青)[/font]

由Admin于周六 八月 31, 2013 7:19 am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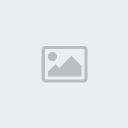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